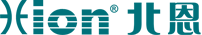ĪČ▓╝╣╚┴ųų▌ĪĘū„š▀ĖĄ├¶║åĮķ ĪČ▓╝╣╚┴ųų▌ĪĘū„š▀ĖĄ├¶║åĮ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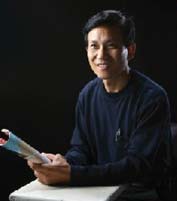 |
ĖĄ├¶Ż¼▒Š├¹ĖČėąį÷Ż¼1967─Ļ│÷╔·ė┌╠½ąą╔Įģ^(q©▒)╝tŲņŪ■Ą─╣╩Ól(xi©Īng)Ī¬Ī¬║ė─Ž┴ųų▌ĪŻąĪīW(xu©”)«ģśI(y©©)║¾Ż¼«ö(d©Īng)▀^▐r(n©«ng)├±Ż¼┤¶▀^╣ż┼’Ż¼┤®▀^▄ŖčbŻ¼ūįīW(xu©”)═Ļ│╔┤¾īŻīW(xu©”)ÜvĪŻ1989─ĻÅ─▓┐ĻĀ▐D(zhu©Żn)śI(y©©)Ż¼Ž╚║¾Å─╩┬ļŖęĢ▐D(zhu©Żn)▓źĪó╬─╗»ą¹é„Ą╚╣żū„Ż¼¼F(xi©żn)×ķ┴ųų▌╩ąą┬┬äųąą─╬─╗»╣żū„╩ęų„╚╬Ż¼░▓Ļ¢╩ąū„ģf(xi©”)Ģ■åTĪó╔ó╬─ģf(xi©”)Ģ■└Ē╩┬Ż¼▒▒Š®ĪČ┐¦Ę╚į┬╣ŌĪĘļsųŠ║×╝sū„╝ęĪŻ
ĪĪĪĪ
ĖĄ├¶ūįėūÉ█║├╬─īW(xu©”)Ż¼18Üqķ_╩╝äė╣Pīæū„▓óŽ“«ö(d©Īng)?sh©┤)žÅV▓źšŠ═ČĖÕŻ¼Å─╩┬īæū„20ėÓ─ĻüĒŻ¼Ž╚║¾į┌ĪČĮŌĘ┼▄Ŗł¾ĪĘĪóųąčļļŖęĢ┼_ĪóĪČ╔Į╬„╚šł¾ĪĘĪóĪČ║ė─Ž╚šł¾ĪĘĪóĪČ║ė─ŽŪÓ─ĻĪĘĪóĪČŪÓ─Ļų«┬ĢĪĘĄ╚ł¾┐»├Į¾w┐»░l(f©Ī)▓ź│÷įŖĖĶĪó╔ó╬─ĪóąĪąĪšfĪół¾Ėµ╬─īW(xu©”)╔Ž░┘Ų¬ĪŻų„ę¬┤·▒Ēū„ŲĘėąļŖęĢäĪĪČ┘ĒįĖĪĘŻ©ųąčļę╗╠ūĪó░╦╠ū▓ź│÷Ż®ĪóļŖęĢļŖė░ĪČįS¢|é}ĪĘęč├µ╩└Ż¼2007─Ļ│÷░µ?zh©©n)Ć╚╦╬─╝»ĪČį┼ų«║█ĪĘŻ¼ČÓŲ¬ū„ŲĘį┌ć°╝ęĪó╩Ī╝ē┘É╩┬ųą½@¬äŻ¼▓┐Ęųā×(y©Łu)ąŃū„ŲĘĮY(ji©”)╝»│÷░µĪŻ |
 ĖĄ├¶ŠÄų°╔ó╬─įŖĖĶ╝»ĪČ▓╝╣╚┴ųų▌ĪĘŠÄūļ╬»åTĢ■├¹å╬ ĖĄ├¶ŠÄų°╔ó╬─įŖĖĶ╝»ĪČ▓╝╣╚┴ųų▌ĪĘŠÄūļ╬»åTĢ■├¹å╬ |
ĪĪĪĪŅÖ ĪĪ å¢Ż║
▓▀ ĪĪ äØŻ║
ų„ ĪĪ ŠÄŻ║
ų„ŠÄų·└ĒŻ║
ŠÄ ĪĪ ╬»Ż║ |
═§┤║░▓ ÓŹųą╚A ĄįĮ©ų▄ ┴║č®╔Į
┤▐Å═(f©┤)╔· ╣∙├„╔· ╔ĻĘ³╔· ╠Ų┼dĒś
ĻÉ║Ż╔· ųņ╬õčĖ ═§śsūµ ŚŅ┼Ó╔Ł
║┬ä”ŲĮ ═§ ║Ļ ĖČæč═¹ ┌w Ę▓
╣∙ųŠ╬─ Ūžų▄Ēś ┤▐ć°╝t ŚŅėŠĮŁ
═§śsūµ
ĖĄ ├¶
ÅłķLŪÓ
═§╔┘Ūõ äóä”└ź äó│»ė┬ äóąg(sh©┤)ŽŃ
╬õŲĮ║Ż └Ņ┤║ėó įŁŠG╔½ ╣∙│╔┴ų
Ūž▒Żųą ═§╬─ÅŖ ╣∙ė±°P ÓćųŠė┬ |
 ĖĄ├¶ŠÄų°╔ó╬─įŖĖĶ╝»ĪČ▓╝╣╚┴ųų▌ĪĘą“ ĖĄ├¶ŠÄų°╔ó╬─įŖĖĶ╝»ĪČ▓╝╣╚┴ųų▌ĪĘą“ |
ĪČ▓╝╣╚┴ųų▌ĪĘą“
┴ųų▌╩ą╬»Ģ°ėøĪĪ═§┤║░▓
|
ĪĪĪĪ┴ųų▌╩Ūę╗Ų¼äō(chu©żng)śI(y©©)Ą─¤ß═┴ĪŻöĄ(sh©┤)╩«─ĻüĒŻ¼Å─ą▐Į©╝tŲņŪ■Ż¼░l(f©Ī)š╣Į©ų■śI(y©©)Ż¼┼d▐kĄžĘĮ╣żśI(y©©)Ż¼ĄĮĮ©įO(sh©©)¼F(xi©żn)┤·╗»┬├ė╬│Ū╩ą║═╔ńĢ■ų„┴xą┬▐r(n©«ng)┤ÕŻ¼Ū┌ä┌Ą─┴ųų▌╚╦├±į┌▀@Ų¼═┴Ąž╔ŽūVīæ┴╦ę╗Ū·Ū·┐╔ĖĶ┐╔Ų³Ą─äō(chu©żng)śI(y©©)ų«ĖĶĪŻ═¼ĢrŻ¼┴ųų▌ėų╩Ūę╗éĆėąų°ėŲŠ├Üv╩ĘĄ─╬─╗»┼c╦ćąg(sh©┤)ų«Ól(xi©Īng)Ż¼╩Ūū„╝ęĪó╦ćąg(sh©┤)╝ęīżšęņ`ĖąĪóš╣╩Š▓┼ŪķĄ─śĘł@ĪŻ▀@ę╗³cŻ¼ĪČ▓╝╣╚┴ųų▌ĪĘĄ─│÷░µ▒Ń╩Ūę╗éĆūC├„ĪŻ
ĪĪĪĪ
ĪČ▓╝╣╚┴ųų▌ĪĘ╩Ūė╔┴ųų▌╩ąą┬┬äųąą─Īó╩ą╬─┬ō(li©ón)║═╩ąū„ģf(xi©”)┬ō(li©ón)║ŽĮM┐ŚŠÄ▌ŗĄ─ę╗▓┐┤¾ą═╬─╝»ĪŻ╬─╝»╩šõø┴╦Į³─ĻüĒę╗┼·┴ųų▌▒Š═┴ū„╝ęäō(chu©żng)ū„Ą─╬─īW(xu©”)ū„ŲĘ╣▓200ėÓŲ¬ĪŻū„š▀ųą╝╚ėąį┌ć°ā╚(n©©i)╬─ē»ŅHŠ▀┬Ģ═¹Ą─└Žū„╝ęĪó└ŽįŖ╚╦Ż¼ėųėąš²į┌┐ĖŲ┴ųų▌╬─īW(xu©”)äō(chu©żng)ū„┤¾ŲņĄ─ŪÓ─Ļū„╝ęŻ¼ę▓ėą¤ßŪķ’¢ØMĪó│§╔µ╬─ē»Ą─īæū„ą┬ąŃĪŻū„ŲĘĘNŅÉ░³└©╔ó╬─ĪóįŖĖĶĪół¾Ėµ╬─īW(xu©”)Ą╚ĪŻū„ŲĘā╚(n©©i)╚▌║Ł╔wĮø(j©®ng)Ø·Īó╔ńĢ■Īó╬─╗»Ą╚Ė„éĆīė├µŻ¼│õĘųš╣¼F(xi©żn)┴╦┴ųų▌Į³─ĻüĒ╬─īW(xu©”)äō(chu©żng)ū„╚ĪĄ├Ą─│╔╣¹Ż¼ę▓╩Ū┴ųų▌╬─īW(xu©”)äō(chu©żng)ū„╦«ŲĮ║═īŹ┴”Ą─ę╗┤╬╚½├µš╣╩ŠĪŻ
ĪĪĪĪ
╬─īW(xu©”)ū„ŲĘĘ┤ė│Ą─ā╚(n©©i)╚▌═∙═∙╩Ūę╗éĆĢr┤·Įø(j©®ng)Ø·║═╔ńĢ■░l(f©Ī)š╣?f©żn)ŅørĄ─┐sė░ĪŻĖ─Ė’ķ_Ę┼ęįüĒŻ¼ė╚Ųõ╩ŪĮ³Äū─ĻüĒŻ¼┴ųų▌Įø(j©®ng)Ø·╔ńĢ■░l(f©Ī)š╣├„’@╝ė┐ņŻ¼╚½╩ąĮø(j©®ng)Ø·Ę▒śsŻ¼╔ńĢ■▀M▓ĮŻ¼╬─╗»š±┼dŻ¼ė┐¼F(xi©żn)│÷┴╦įSČÓą┬╩┬╬’Īóą┬Š░Ž¾Ż¼╚╦éāĄ─╦╝Žļė^─Ņ║═Š½╔±ūĘŪ¾ę▓į┌▓╗öÓ░l(f©Ī)╔·ų°ą┬Ą─ūā╗»Ż¼▀@ą®Č╝×ķ╬─īW(xu©”)äō(chu©żng)ū„╠ß╣®┴╦ÅVķ¤Ą─┐šķgŻ¼ę▓×ķŲõ╠ß╣®┴╦┤¾┴┐╔·äėĄ─äō(chu©żng)ū„╦ž▓─ĪŻĪČ▓╝╣╚┴ųų▌ĪĘ╬─╝»Ą─ū„š▀éāęįūį╝║├¶õJĄ─ė|ĮŪ£╩(zh©│n)┤_Ąž░č╬šūĪ┴╦▀@éĆĢr┤·╚╦éāĄ─╦╝ŽļŪķĖąŻ¼ė├ūį╝║Ą─╣PīæŽ┬┴╦░l(f©Ī)š╣ūā╗»ų°Ą─▀@éĆ╔ńĢ■Ż¼ęį╝░▀@éĆ╔ńĢ■▓╗═¼╚╦éāĄ─ā╚(n©©i)ą─╩└ĮńĪŻ╦¹éā╗“ųÄĖĶĢr┤·Ą─ūā╗»Ż¼╗“├Ķ└L╝ęÓl(xi©Īng)Ą─╔Į╦«Ż¼╗“╩Ń░l(f©Ī)éĆ╚╦Ą─ŪķæčŻ¼Å─ę╗éƬÜ╠žĄ─ęĢĮŪš█╔õ│÷┴╦┴ųų▌Ą─░l(f©Ī)š╣ūā╗»Ż¼Įo╚╦éāĘŅ½I╔Ž┴╦ę╗Ę▌žS╩óĄ─Š½╔±╩│╝ZĪŻ«ö(d©Īng)╚╦éā┼§ŠĒį┌╩ųŻ¼ė├ą─ŲĘ╬Č▀@ą®╬─ūųĢrŻ¼Č©Ģ■┼cū„ŲĘųą╦∙▒Ē¼F(xi©żn)Ą─╝ęÓl(xi©Īng)╚╦Īó╝ęÓl(xi©Īng)╩┬Īó╝ęÓl(xi©Īng)Ūķę²ŲÅŖ┴ęĄ─╣▓°QĪŻ
ĪĪĪĪ
╝ėÅŖŠ½╔±╬─├„Į©įO(sh©©)Ż¼▓╗öÓĘ▒śs╬─īW(xu©”)äō(chu©żng)ū„Ż¼┼¼┴”ØMūŃ╚╦éā?n©©i)šęµį÷ķLĄ─Š½╔±╬─╗»ąĶŪ¾Ż¼╩Ū╚½├µĮ©įO(sh©©)ąĪ┐Ą╔ńĢ■Ą─ųžę¬ā╚(n©©i)╚▌ų«ę╗Ż¼ę▓╩Ū┬õīŹ┐ŲīW(xu©”)░l(f©Ī)š╣ė^Īóśŗ(g©░u)Į©║═ųC╔ńĢ■Ą─▒ž╚╗ę¬Ū¾ĪŻĪ░╩«ę╗╬ÕĪ▒Ų┌ķgŻ¼╬ę╩Ī╠ß│÷┴╦Į©įO(sh©©)╬─╗»ÅŖ╩ĪĄ─║Ļéź─┐ś╦(bi©Īo)Ż¼░▓Ļ¢╩ą╠ß│÷┴╦╬─╗»┼d╩ąĄ─░l(f©Ī)š╣æ(zh©żn)┬įŻ¼╬ę╩ąę▓š²į┌ĘeśO═Ų▀M╬─╗»«a(ch©Żn)śI(y©©)Ą─░l(f©Ī)š╣ĪŻÅ─▀@éĆęŌ┴x╔ŽųvŻ¼Ę▒śs╬─īW(xu©”)äō(chu©żng)ū„Ż¼╝ė┐ņ╬─╗»╩┬śI(y©©)Ą─░l(f©Ī)š╣Ż¼ę▓╩Ū╬ęéāę╗ĒŚ┴x▓╗╚▌▐oĄ─ž¤(z©”)╚╬ĪŻ┴ųų▌Ą─╬─īW(xu©”)äō(chu©żng)ū„š▀æ¬(y©®ng)ų„äėō·(d©Īn)«ö(d©Īng)Ų▀@Ę▌ųž╚╬Ż¼╔Ņ╚ļĄĮ╔·╗Ņųą╚źŻ¼╔Ņ╚ļĄĮ╚║▒Ŗųą╚źŻ¼ŠoŠo░č╬šĢr┤·├}▓½Ż¼╝żØßōPŪÕŻ¼äō(chu©żng)ū„│÷Ė³ČÓŠ▀ėą§r├„Ģr┤·╠ž╔½Īó░║ōPŽ“╔ŽĪóā╚(n©©i)╚▌│õīŹĪó╚║▒ŖŽ▓┬äśĘęŖĄ─╬─īW(xu©”)ū„ŲĘŻ¼ė├▀@ą®ā×(y©Łu)ąŃĄ─ū„ŲĘ╚źĖą╚Š╚╦Īó╣─╬Ķ╚╦ĪóĮ╠ė²╚╦ĪŻ▀@ī”╠ßĖ▀╬ę╩ą╚║▒ŖĄ─╬─╗»╦žB(y©Żng)Ż¼┤┘▀M╚½╩ąĮø(j©®ng)Ø·╔ńĢ■Ą─ģf(xi©”)š{(di©żo)░l(f©Ī)š╣Ż¼╠ßĖ▀╬ę╩ąš¹¾wīŹ┴”║═ŠC║ŽĖéĀÄ┴”Ż¼Č╝Š▀ėą╩«Ęųųžę¬Ą─ęŌ┴xĪŻ
ĪĪĪĪ
éź┤¾Ą─Ģr┤·ąĶę¬éź┤¾Ą─╣─╩ų×ķų«╣─┼c║¶ĪŻš²į┌’w╦┘░l(f©Ī)š╣ūā╗»ų°Ą─┴ųų▌Ż¼ąĶę¬ėąĖ³ČÓĄ─╚╦═Č╔ĒĄĮ╬─īW(xu©”)äō(chu©żng)ū„ųąüĒŻ¼ō]äėŲ╩ųųąĄ─╣PŻ¼īæŽ┬▀@ĘNūā╗»ųąĄ─╚fŪ¦Š░Ž¾ĪŻĪČ▓╝╣╚┴ųų▌ĪĘ╬─╝»Ą─│÷░µŻ¼▓╗āH╩Ūī”▀^╚źÄū─ĻüĒ┴ųų▌╬─īW(xu©”)äō(chu©żng)ū„Ą─ę╗éĆ┐éĮY(ji©”)Ż¼Ė³╩Ūę╗éĆą┬Ą─Ų³cŻ¼šč╩Šų°╬ę╩ąĖ³╝ėĮk¹ÉČÓū╦Ą─╬─īW(xu©”)äō(chu©żng)ū„┤║╠ņĄ─üĒ┼RĪŻ |
▓╝╣╚ų«°Qé„Ól(xi©Īng)ę¶
Ī¬Ī¬ ą“ĪČ▓╝╣╚┴ųų▌ĪĘ
ŚŅ╔┘║Ō |
ĪĪĪĪąĪ¹£īó╩ņ╝Š╣Ø(ji©”)Ż¼▓╝╣╚°Bį┌įŁę░╔Ž’wŽĶĪŻĪ░▓╝╣╚▓╝╣╚Ż¼ąQ└Ž¹£?zh©│n)ņĪ▒Ż¼▓╝╣╚ų«°Q╦─┬Ģę╗Č╚Ż¼ŪÕ┴┴é„▓╝ĪŻ╬ęį┌ĪČ▓╝╣╚┴ųų▌ĪĘ└’ūxĄĮ┴╦▀@śėĄ─├Ķ└LŻ¼ļ[ļ[╝s╝s╦Ų║§┬ĀĄĮ▀hĘĮĄ─ĻćĻć°Q│¬Ż¼ą─ųąė┐┴„ų°╩š½@Ą─ą└Ž▓║═ĖąäėĪŻ
ĪČ▓╝╣╚┴ųų▌ĪĘ╩Ū┴ųų▌╩ąą┬┬äųąą─Īó╩ą╬─┬ō(li©ón)║═╩ąū„ģf(xi©”)┬ō(li©ón)║ŽĮM┐ŚŠÄ▌ŗĄ─┴ųų▌╩ąĄ┌ę╗▓┐┤¾ą═╬─╝»Ż¼ų╝į┌╚½├µĘ┤ė│┴ųų▌╔ńĢ■▀M▓ĮĪóĮø(j©®ng)Ø·Ę▒śsĄ─┤¾║├ą╬ä▌Ż¼š±┼d┴ųų▌╬─╗»╩┬śI(y©©)Ż¼š╣╩Š╬─īW(xu©”)äō(chu©żng)ū„│╔╣¹ĪŻ┴ųų▌Ą─┼¾ėčéāį┌ŠÄ▌ŗ▒ŠĢ°ĢrĮo╬ęé„üĒĢ°ĖÕŻ¼┤“üĒļŖįÆŻ¼č¹╬ęę╗ą“Ż¼ūī╬ęŅHėX╗╠┐ųĪŻ╬ę╔·╗Ņė┌¢|─Ž║Ż×IŻ¼ę╗Ž“╔±═∙ė┌╣╩Ól(xi©Īng)┴ųų▌Ż¼┬ō(li©ón)ŽĄ║═┴╦ĮŌĄ─Ū■Ą└ģs▓╗ČÓŻ¼║▄ō·(d©Īn)ą─čįų«▓╗ę╦Ż¼ėąŃŻ║├ęŌĪŻūx┴TĢ°ĖÕŻ¼┼dŖ^ų«Ėąė═╚╗Č°╔·Ż¼ė┌╩ŪŠ═╠ß╣PĢ│čįŻ¼┴─▒ĒĖą┐«Ż¼╗“─▄╠ß╣®▀hĘĮÓl(xi©Īng)ėHĄ─┴Ēę╗ĘNęĢĮŪŻ┐
ĪČ▓╝╣╚┴ųų▌ĪĘūī╬ęėąę╗ĘN╔±ė╬╣╩═┴ų«ĖąĪŻ╬ę╩Ū┴ųų▌╝«╚╦Ż¼╔Ž╩└╝o(j©¼)80─Ļ┤·į°ÜwĘĄ╣╩Ól(xi©Īng)╩ĪėHŻ¼ė╔ė┌ĢrķgČ╠Ģ║Ż¼ī”╣╩Ól(xi©Īng)Ą─ėĪŽ¾śO╔ŅŻ¼▓Į┬─ģs£\Ż¼ū▀Ą─ĄžĘĮ║▄╔┘Ż¼│Żć@×ķ╚▒║ČĪŻ▀@▒ŠĢ°į┌╬ę├µŪ░š╣¼F(xi©żn)┴╦╣╩Ól(xi©Īng)┤¾┴┐Ą─╔Į┤©«ŗ├µ║═’L(f©źng)╬’łDŠ░Ż¼§r├„Č°╔·äėĪŻ╬ęį┌Ģ°└’┐┤ĄĮ┴╦╬Ī╬Ī╠½ąąŻ¼ė╬Üv┴╦┤¾Ź{╣╚Ż¼ū▀▀M┴╦č®╣Ō╦┬Ż¼ų¬Ą└┴╦ę”┤ÕĄ─╦«║ėŻ¼░l(f©Ī)¼F(xi©żn)┴╦┤║Ū’æ(zh©żn)ć°Ģr┤·┌w╬õņ`═§ą▐Į©Ą─ę╗Č╬ķL│ŪĪŻ╠½ąą╔Į╔Žėąę╗éĆ╔±ŲµĄ─╔n²łČ┤Ż¼Ž╔┼_╔Į╔ĮĒö¢|█±┤Õ├±ķ_▐k┴╦╝ę═ź┬├╔ńŻ¼įSįSČÓČÓĄ─’L(f©źng)═┴Š░╬’Ħų°ūį╚╗Ą─ŪÕą┬║═Üv╩ĘĄ─║±ųžŻ¼═©▀^╣Pš▀│õØMŪķĖąĄ─╣Pė|į┌╬ęĄ─č█Ū░│╩¼F(xi©żn)ĪŻ╬┤į°╔ĒĮ³Ż¼ėą╚ńėH┼RĪŻ
ĪĪĪĪ
▀@▒ŠĢ°ūī╬ęĖ±═ŌĖąė|Ą─▀Ćėą╚╦╬’ĪŻ╦∙ų^Ī░ėH▓╗ėHŻ¼╣╩Ól(xi©Īng)╚╦Ī▒Ż¼╣╩Ól(xi©Īng)╚╦╬’ūŅĀ┐▀hĘĮÓl(xi©Īng)╚╦ĪŻĪČ▓╝╣╚┴ųų▌ĪĘ└’Ż¼▓╗šō╔ó╬─ĪóįŖĖĶ▀Ć╩Ūł¾Ėµ╬─īW(xu©”)ū„ŲĘŻ¼┴ųų▌╚╦╬’¤o╠Ä▓╗į┌Ż¼Ķ“Ķ“╚ń╔·ĪŻ╬ęį┌Ģ°└’ęŖĄĮ┴╦ę╗ą®┴ųų▌Ą─Üv╩ĘėóĮ▄Ż¼└²╚ń├„│»─Ļķgį┌┴ų╚╬╦──Ļų¬┐hĄ─ųx╦╝┬öŻ¼╦¹╚ļ╔Į▓ņ╦«Ż¼ĮM┐Ś╩³├±ą▐Į©▒╗ūu×ķĪ░ųx╣½Ū■Ī▒Ą─║ķ╣╚Ū■Ż¼Ū■ķL18╚A└’Ż¼ĮŌøQ┴╦40ėÓ┤ÕĄ─╚╦ą¾ė├╦«ĪŻ┐╣æ(zh©żn)Ų┌ķgėąę╗╬╗ąņŠĖ▀hīó▄ŖŻ¼į┌┴ų┐h┼c░╦┬Ę▄Ŗ├▄Ūą┼õ║ŽŻ¼▐D(zhu©Żn)æ(zh©żn)╠½ąąŖ^ė┬Üóö│ĪŻĮŌĘ┼æ(zh©żn)ĀÄŲ┌ķgŻ¼┤¾┼·┴ų┐hĖ╔▓┐š¹čb▀hąąŻ¼×ķĮŌĘ┼╚½ųąć°║═Į©įO(sh©©)ą┬ųąć°ū÷│÷Š▐┤¾žĢ½IŻ¼Ģ°└’īæ╝░Ą─╣╚╬─▓²Š═╩ŪŲõųąĮ▄│÷┤·▒ĒĪŻ«ö(d©Īng)┤·┴ųų▌┤¾ĄžĄ─Ž╚─Żį┌Ģ°└’Ė³ėą═╗│÷▒Ē¼F(xi©żn)Ż¼└ŽĢ°ėøŚŅ┘F╝░Ųõæ(zh©żn)ėčĦŅI(l©½ng)┴ų┐h╚╦├±ą▐Į©┴╦┼e╩└┬ä├¹Ą─╝tŲņŪ■Ż¼┘ØĖĶĪ░┼³ķ_╠½ąą╔ĮŻ¼š─║ė┤®╔ĮüĒŻ¼┴ų┐h╚╦├±ČÓēčųŠŻ¼╩─░č╔Į║ėųž░▓┼┼ĪŻĪ▒ĒæÅž╔±ų▌ĪŻą▐Į©╝tŲņŪ■ĢrĄ─╚║▒Ŗėóą█╔Ēė░ę▓į┌╬─╝»ųą╗Ņ▄SŻ║ĪČę╣╦▐Ī░Ę“Ų▐Ī▒Ę┐ĪĘ└’Ż¼ę╗ī”ą┬╚╦į┌╣żĄžĪ░Ę“Ų▐Ī▒Ę┐ūĪ┴╦ę╗ę╣Ż¼▀@Ę┐ūė╩ŪĪ░╬╗ė┌ę╗éĆ┤¾╔Į─_Ž┬Ą─┤¾Är╩»┐pŻ¼Š═ų°ļ[ļ[Ą─╗╣Ō┐┤┤¾╝sėą░ļ╣½└’ķLŻ¼╔ĮÄr┐pĄ─▒▒▀ģė├ąĪ╩»░Õę╗īėę╗īėĄžēŠų°Ż¼═Ė▀^╩»┐p─▄┐┤ĄĮūĪį┌└’├µĄ─├±╣żĪŻĪ▒╣Pš▀Ą─Ų▐ūė«ö(d©Īng)═Ē│įĄ─╩ŪŽĪ’łŻ¼╝t╩Ē├µ┐ĘŻ¼Ė╔╝t╩Ē╚~Ż¼«ö(d©Īng)╠ņÅ─š─║ė▀ģ═∙Ū■░Č╔Ž╠¦╔│Ż¼░ļ╠ņ╠¦8įŌŻ¼═╚└█Ą─╠█Ż¼╝ń░“─[╣─Ą├└ŽĖ▀Ż¼ę╗▀ģ┼cš╔Ę“šfų°įÆŻ¼ę╗▀ģŠ═║¶║¶╚ļ╦»ĪŻŅÉ╦Ų├Ķ└LśOŲõśŃīŹŻ¼ę▓śOŲõšµŪąĄžį┘¼F(xi©żn)┴╦«ö(d©Īng)─ĻłDŠ░Ż¼┴Ņ╚╦ūxüĒļy═³ĪŻĪČ▓╝╣╚┴ųų▌ĪĘ└’▀Ćėą┤¾┴┐▒Ē¼F(xi©żn)ĢrŽ┬┴ųų▌╚╦╔·╗Ņ┼cŪķĖąĄ─ū„ŲĘŻ║▐r(n©«ng)╝ę╚╦┘užiŻ¼║”┼┬ži┬ĀČ«┴╦▓╗│į╩│Ż¼Ą├šfĪ░│÷╚”Ī▒ĪŻ╩«╚f├±╣ż│÷╠½ąąŻ¼▒╝Ė░╠ņ─Ž║Ż▒▒Ż¼Į©įO(sh©©)ūµć°╦─ĘĮŻ¼Ī░Žļ╝ęĄ─Ģr║“╬ęŠ══¹ų°╠ņĪ▒ĪŻ╔ó╬─▌ŗ║═įŖĖĶ▌ŗĄ─┤¾┴┐ū„ŲĘ└’Ż¼Ól(xi©Īng)ŪķĪóėHŪķĄ─├Ķ└L╠Ä╠Ä╝Üų┬äė╚╦ĪŻ
ĪĪĪĪ
ĪČ▓╝╣╚┴ųų▌ĪĘ└’┴Ēėąę╗┼·╚╦╬’ūī╬ę▒ČėXūųžŻ¼Š═╩Ū╦³Ą─ū„š▀║═ŠÄš▀éāĪŻ┴ųų▌Ąžņ`╚╦Į▄Ż¼ėó▓┼▌ģ│÷Ż¼ę▓│õĘų¾w¼F(xi©żn)į┌▒ŠĢ°Ą─ū„š▀ŠÄš▀╔Ē╔ŽĪŻō■(j©┤)╬ę╦∙┬äŻ¼▀@▒Š╬─╝»Ž“╚½╩ąū„╝ęĪó╬─īW(xu©”)É█║├š▀š„ĖÕŻ¼ÜvĢr╩«éĆį┬Ż¼╣▓╩šĄĮüĒĖÕ500ėÓŲ¬Ż©╩ūŻ®Ż¼Įø(j©®ng)▀^Š½ą─║Y▀x║¾Ż¼╚ļŠÄĖÕ╝■200ėÓŲ¬Ż©╩ūŻ®ĪŻŲõųąėą┴ųų▌╩ąŅHŠ▀┬Ģ═¹Ą─└Žū„╝ęĪó└ŽįŖ╚╦Ż¼ėą’L(f©źng)╚Aš²├»Ą─ŪÓ─Ļū„š▀Ż¼ėą¤ßŪķ’¢ØMĄ─īæū„ą┬ąŃŻ¼│õĘųš╣¼F(xi©żn)┴╦┴ųų▌╬─īW(xu©”)äō(chu©żng)ū„ĻĀ╬ķĄ─ęÄ(gu©®)─Ż║═īŹ┴”ĪŻ┴ųų▌Ą─ū„╝ę└’Ż¼╬ęįŁ▒Šų╗ų¬Ą└ę╗╬╗┤▐Å═(f©┤)╔·Ž╚╔·ĪŻ╬ęūx▀^╦¹Ą─ąĪšfŻ¼ČÓ─ĻŪ░ę“×ķę╗éĆÖCŠē┼c╦¹ėą▀^┬ō(li©ón)ŽĄĪŻį┌ĪČ▓╝╣╚┴ųų▌ĪĘ└’ūxĄĮ┤▐Ž╚╔·īæĄ─ĪČ╩ųĪĘŻ¼ĖąėX╠žäeėHŪąĪŻ╬ęūóęŌĄĮ╬─╝»ųąČÓ╬╗╬─ėčį┌╬─š┬└’╠ߥĮ╦¹Ż¼Å─ųąĖąų¬Å─╔Ž╩└╝o(j©¼)╬ÕĪó┴∙╩«─Ļ┤·ĄĮ╚ńĮ±Ż¼┤▐Ž╚╔·╣PĖ¹▓╗▌zŻ¼¤ßą─ĮM┐Ś╬─īW(xu©”)╗ŅäėŻ¼Ę÷ų▓╬─īW(xu©”)ą┬╚╦Ą─╩┬█EŻ¼ę“┤╦Ė±═ŌÜJ┼ÕĪŻĪČ▓╝╣╚┴ųų▌ĪĘĄ─įSČÓįŖ╬─ū„ŲĘ║═ąĪąĪšfĄ─╦ćąg(sh©┤)│╔Š═┴Ņ╬ęėĪŽ¾╔Ņ┐╠Ż¼▀@ę╗╬─╗»ĒŚ─┐¤oę╔╩Ūį┌«ö(d©Īng)?sh©┤)ž³hš■ŅI(l©½ng)ī¦(d©Żo)║═ŽÓĻP(gu©Īn)▓┐ķTĄ─ųžęĢŽ┬═Ļ│╔Ą─Ż¼│ąō·(d©Īn)Š▀¾wŠÄ▌ŗ╚╬äš(w©┤)Ą─═¼ųŠĖČ│÷┴╦¤oöĄ(sh©┤)ą─č¬ĪŻ▀@▒ŠĢ°į┌š╣¼F(xi©żn)┴ųų▌’L(f©źng)├▓Ą─═¼ĢrŻ¼ę▓š╣¼F(xi©żn)┴╦┴ųų▌Š½╔±╬─├„Į©įO(sh©©)Ą─│╔╣¹Ż¼╬─īW(xu©”)╩┬śI(y©©)Ą─░l(f©Ī)š╣║═╬─īW(xu©”)╚╦▓┼Ą─ÅŖ┤¾Ļć╚▌ĪŻ
ĪĪĪĪ
ę“┤╦║▄×ķĪČ▓╝╣╚┴ųų▌ĪĘĄ─│÷░µĖąĄĮĖ▀┼dŻ¼×ķūį╝║Ą─╣╩Ól(xi©Īng)ĖąĄĮūį║└ĪŻ
Ż©ŚŅ╔┘║ŌŻ¼1953─Ļ╔·ė┌ĖŻĮ©╩Īš─ų▌╩ąŻ¼ūµ╝«┴ųų▌╩ą¢|ŹÅµé(zh©©n)▒▒ČĪę▒┤ÕŻ¼¼F(xi©żn)╚╬ĖŻĮ©╩Ī╬─┬ō(li©ón)Ė▒ų„Ž»Īóųąć°ū„╝ęģf(xi©”)Ģ■Ģ■åTŻ® |
ą“
┤▐Å═(f©┤)╔· |
ĪĪĪĪ┴ųų▌╩ąŻ©įŁ┴ų┐hŻ®═┴▒Ī╩»║±Ż¼Üv╩Ę╔ŽĖ╔║Ą×─(z©Īi)╗─Ņl░l(f©Ī)ĪŻ├±ęį╩│×ķ╠ņŻ¼Į^┤¾ČÓöĄ(sh©┤)┴ų┐h╚╦Ż¼ąĪąĪ─Ļ╝o(j©¼)▒Ń═Ō│÷┤“╣żīW(xu©”)═ĮĪ░┌sūņĪ▒Ż¼Ī░▓╗│į═ŌĄž╝Z▓╗─▄▀^Ģr╣ŌĪ▒čėé„┴╦╔ŽŪ¦─ĻĪŻ▀@╩ŪŚl╝■įņŠ═Ą─Üv╩ĘŻ¼į┌▀@ĘNŚl╝■Ž┬Ż¼░┘ąš║╬ŠēūxĢ°īæūųŻ┐▓╗ūRūųĖ³šä▓╗╔ŽįŖį~╬─š┬ĪŻ╝┤╩╣éĆäeĖ╗æ¶╣┘╗┬╚╦╝ęŻ¼ęÓęįĪ░Ė¹ūxĪ▒×ķųžŻ¼╬Ķ┼¬╬──½š▀┴╚┴╚Ż¼╣╩šµš²┴ų┐h╚╦é„Ž┬üĒĄ──½█E╔§╔┘ĪŻ
ĪĪĪĪ
ų▒ĄĮĮ³┤·Ż¼ļSų°Ģr┤·Ą─Ė³╠µŻ¼▓┼ėą┴╦▐D(zhu©Żn)ÖCŻ¼é„Įy(t©»ng)Ą─├±▓╗ūRČĪĄ─Üv╩ĘĖ±Šų▓┼▒╗┤“ŲŲĪŻĄ½╬─┼c▒ŖĄ─šµš²╚┌║ŽŻ¼▀Ć╩Ūį┌ųą╚A╚╦├±╣▓║═ć°│╔┴óĄ─Ū░║¾ĪŻŽ╚╩Ū20╩└╝o(j©¼)40─Ļ┤·Ż¼░╦┬Ę▄ŖüĒ┴╦Ż¼╣▓«a(ch©Żn)³hüĒ┴╦Ż¼ĮŌĘ┼┴╦ĪŻ▀@3éĆĪ░┴╦Ī▒Ż¼ĮY(ji©”)╩°┴╦įSČÓėųķ_äō(chu©żng)┴╦įSČÓĪŻ═┴Ė─ĢrŲ┌Ż¼└¹ė├╚║▒ŖĘŁ╔Ē«ö(d©Īng)╝ęū÷ų„Ą─ĘeśOąįŻ¼┴ų┐hĖ„┤Õ▒Ń│╔┴óŲĪ░▐r(n©«ng)┤ÕŠŃśĘ▓┐Ī▒▀\ė├╚║▒ŖŽ▓┬äśĘęŖĄ─ą╬╩ĮŻ¼┼õ║Ž╣żū„ųąą─Ż¼┤¾ĖŃą¹é„ĪČ═§┘F┼c└ŅŽŃŽŃĪĘĪóĪČ░ū├½┼«ĪĘĪóĪČč¬£I│ĪĘĄ╚ą┬æ“╝ęė„æ¶ĢįŻ¼Ė³ėąę╗┤¾┼·ūįŠÄūįč▌Ą─╣Ø(ji©”)─┐į┌Ė„┤Õ╔Žč▌Ż¼╩šĄĮ║▄║├Ą─ą¦╣¹ĪŻ«ö(d©Īng)Ģr╚½┐hūŅėą├¹Ą─äĪłF│÷į┌║ėĒśĪó¢|ŹÅĪó║ŽØŠĪó╚╬┤Õ4éĆÓl(xi©Īng)µé(zh©©n)Ż¼║ėĒśµé(zh©©n)└╔ēŠ┤Õę╗éĆ┤ÕŠ═│÷▀^╚²éĆĖC░ÓŻ¼║¾║Ž▓ó×ķą┬╚AäĪłFĪŻ┼ÓB(y©Żng)┴╦ę╗┤¾┼·č▌ŠÄī¦(d©Żo)╚╦åTŻ¼ų▄ī¦(d©Żo)╚╩ĪóČŁ░l(f©Ī)ŲµĪóÅł╔·ę╗Īó╔Żė±▓²Ą╚Ż¼Č╝╩Ū─ŪĢr┤·Ą─├¹╚╦ĪŻ«ö(d©Īng)ĢręčĮø(j©®ng)│÷¼F(xi©żn)═┴╔·═┴ķLĄ─╬─īW(xu©”)äō(chu©żng)ū„├╚č┐ĪŻ
ĪĪĪĪ
─ŪĢr║“Ż¼░╦┬Ę▄Ŗ╣▓«a(ch©Żn)³hį┌╚šę╣×ķ░┘ąš▐k║├╩┬ų\ąęĖŻŻ¼╠žäe╩ŪäėåT░┘ąšīW(xu©”)╬─╗»Īó╔ŽČ¼īW(xu©”)Īó╔Ž├±ąŻĪóÆ▀├żĪŻė╔ÅŖųŲĄĮūįįĖŻ¼ą╬│╔Äū┤╬╚½├±īW(xu©”)╬─╗»Ė▀│▒Ż¼│÷¼F(xi©żn)┴╦╚½ć°Ž╚▀MĄõą═Ż¼║ŽØŠÓl(xi©Īng)┤¾─Ž╔Į┤Õę╗─Ļ╦─╝Š└ū┤“▓╗╔óĄ─Ī░ĶF├±ąŻĪ▒ĪŻ┤Õ┤Õ┤ÕŅ^ėą╚╦ėąūųĄ─Ī░ūRūųŹÅĄĮ╠ÄėąŻ¼▓╗ūRūų▓╗─▄ū▀Ī▒ĪŻŠ═╩Ūį┌▀@ĘN▒│Š░Ž┬Ż¼▓┼ė┐¼F(xi©żn)│÷┴╦▓╔╔ŻÓl(xi©Īng)─ŽŠ░╔½┤Õ┐ņ░ÕįŖ╚╦ŪžęūĪŻ1951─ĻŠ═├¹ōPŲĮįŁ╩ĪĪŻ▓┼ėą┴╦╔ĻØh╚²Īó╩»ė±ĄŅĪó╣∙ė±ĘÕĄ╚ę╗┼·┐ņ░ÕĪóĒś┐┌┴’Ą─ŠÄš▀┼cšfš▀ĪŻ▓┼ėą┴╦║ŽØŠÓl(xi©Īng)¢|╔ĮĄū┤ÕŪÓ─Ļ┤▐▓┼²łīæĄ─ā║═»╬─īW(xu©”)Ī░▓╔śõūčā║Ī▒į┌╩Ī╝ē┐»╬’ĪČĘŁ╔Ē╬─╦ćĪĘ╔Ž░l(f©Ī)▒Ē▓ó½@┴╦¬äĪŻ▓┼²łė├╦∙Ą├Ą─¬äĮ┘I┴╦ę╗╝■├½─žūėųą╔ĮĘ■Ż¼Ė▀┼dĢr▓┼Å─Žõūė└’╚Ī│÷üĒ┤®ā╔╠ņĪŻ┤╦Ūķ┤╦Š░į┌┴ųų▌Üv╩Ę╔Ž╩Ū¬Üę╗¤oČ■Ą─ĪŻ
ĪĪĪĪ
1955─ĻŻ¼╣Pš▀Å─╔Į╬„╩ĪķLų╬╩ąĘĄ╗ž╣╩Ól(xi©Īng)║¾Ż¼ą─└’╔Ņ▓žų°Ž“┌wśõ└ĒīW(xu©”)┴Ģ(x©¬)Ą──┐ś╦(bi©Īo)Ż¼1956─Ļ2į┬į┌║ė─Ž╚šł¾░l(f©Ī)▒Ē╠Ä┼«ū„ŲĘ║¾Ż¼▒ŃśõŲĖ³┤¾Ą─øQą─║═ą┼ą─Ż¼▒ŃĮė▀B▓╗öÓėąū„ŲĘ░l(f©Ī)▒ĒĪŻ▀@ūį╚╗ė░ĒæĄĮ┴╦ę╗┼·ėą╬─╗»Ą─ŪÓ─Ļ╚╦Ż¼ų▒Įė╗“ķgĮėīW(xu©”)┴Ģ(x©¬)Į╗┴„║¾▀M▓Į╩«Ęų┐ņŻ¼Č╠Č╠Äū─ĻķgŻ¼±R╝ę╔Į┤Õ┤▐├„╔ĮĪó╔Ļ┤Õģ╬╣╔·Īó╣∙Ę©╔·Ż¼╬„Ū·Ļ¢┤ÕŪ·║»ąŪĪóŪ·┴∙į¬Ż¼╬„žS┤Õ╣∙ė±ĘÕŻ¼¢|ę▒┤Õį└░l(f©Ī)╚ńĄ╚ęčį┌╩Ī╝ēęį╔Žł¾┐»░l(f©Ī)▒Ē╬─š┬ĪŻ╚½┐hĄ─Ī░īæ╝ęĪ▒ęčĮø(j©®ng)ų▓Įą╬│╔┴╦ąĪÜŌ║“ĪŻė╚Ųõ╩Ū1965─Ļ╣Pš▀ĄĮ▒▒Š®│÷Ž»╚½ć°ŪÓäō(chu©żng)Ģ■Ż¼ī”▒Š╚╦ī”▒Š┐h╬─īW(xu©”)ū„š▀╣─╬Ķ║▄┤¾Ż¼┴óųŠÅ─╬─ą┼ą─Ė³ūŃĪŻ╬ę┐h╬─īW(xu©”)äō(chu©żng)ū„╝┤īó│÷¼F(xi©żn)┐╔Ž▓Ą─Ė▀│▒ĢrŻ¼╬─╗»┤¾Ė’├³ķ_╩╝┴╦ĪŻ
ĪĪĪĪ
╬─Ė’║¾Ż¼┴ų┐hėų├░│÷üĒę╗┼·Ī░īæ╝ęĪ▒Ż¼╦¹éāķgĮė╗“ų▒Įė╩▄ĄĮ▀^╬ęĄ─ķLŲ¬ąĪšfĪČ╠½ąąųŠĪĘė░ĒæŻ¼ę“×ķ─ŪĢrĄ─╚╦▀Ćå╬╝ā▀Ć▒ŠĘųŻ¼Å─╬─▀Ć╩Ūę╗Śl║▄▒╗╚╦Ų„ųžĄ─▌x╗═┬ĘĪŻ╬─Ė’║¾┼c╬ęĮėė|▌^ČÓĄ─╬─īW(xu©”)ū„š▀ėąäóĘ©ą▐ĪóÅł▀\╔ĮĪó│Ż┐ĪĮ▄ĪóĻÉ║Ż╔·Īó╠Ų┼dĒśĪóÅł▄Ä£YĪó║┬Į©╔·ĪóäóÅV╝¬Īó└Ņ▀\Ę©Īó═§║Ļ├±ĪóŚŅėŠĮŁĪó╬║┐ĪÅ®Īó║┬Ēś▓┼Īó╣∙▓╝╦┤Īó└Ņ├„ĒśĪó└Ņ├„╔·ĪóŚŅć°ųęĪóį└┴ųŠšĪó┬Ę╬─ĮŁĄ╚ĪŻĄ½┴ų┐h╬─ē»šµš²ĘQĄ├╔Žū„š▀ū„ŲĘ╚ńėĻ║¾┤║╣SŻ¼▀Ć╩Ūį┌20╩└╝o(j©¼)80─Ļ┤·Ė─Ė’ķ_Ę┼║¾ĪŻę╗╩Ū╦╝ŽļĮŌĘ┼Ż¼Š½╔±ø]┴╦ē║┴”Ż╗Č■╩Ū╬’┘|(zh©¼)╔·╗Ņ╠ßĖ▀Ż¼▓╗ė├į┘×ķĪ░┌sūņĪ▒░l(f©Ī)│ŅŻ╗╚²╩Ū╬─╗»ų¬ūRŲš╝░╠ßĖ▀ĪŻį┌▀@śėĄ─╩│’¢ę┬┼»ųąŻ¼▓┼┐╔ęįšµš²ŅÖ╝░ĄĮ╬─īW(xu©”)ĪŻ▀@śėĄ─═┴╚└ųąŻ¼ėų╔·ķL│÷┴╦ę╗┼·║▄ėą▓┼╚Aėų║▄─Ļ▌pĄ─Ī░īæ╝ęĪ▒╚ńįŁŠG╔½Īó║┬ä”ŲĮĪóųņ╬õčĖĪóĖĄ├¶Īóäóąg(sh©┤)ŽŃĪó╣∙ÅŖĪó╣∙│╔┴ųĪóŚŅųŠėŅĪó╣∙Ū’ŠšĪó╬┤Ģį├„Īóäó┴ųĖŻĪóŚŅ▄ŖÅŖĪó└Ņ╚f╚½Ą╚ĪŻ▀@ę╗ų¦╔·┴”▄ŖĄ─╝ė╚ļŻ¼╩╣Ą├┴ų┐h╬─ł@šµš²ėŁüĒ┴╦┤║╠ņĪŻĄĮ90─Ļ┤·Ż¼ėųėąę╗┼·Ų³cĖ▀īŹ┴”ÅŖŻ¼Ė³─Ļ▌pĄ─╬─īW(xu©”)ą┬╚╦├░│÷üĒŻ¼╚ń░ū┼dč┼Īó╩»╔ĮŪÓĪó╣∙É█Ą┬Īó╔ą┤õĘ╝ĪóŚŅė±¢|ĪóŚŅزĄ╚Ż¼╩╣Ą├┴ųų▌╬─╩┬Ė³╝ė╗Ņ▄SĪŻ
ĪĪĪĪ
ų┴Į±Ż¼┴ųų▌╩ą└ŽųąŪÓ╚²┤·ū„š▀║Ž┴„Ż¼ęčą╬│╔ę╗ų¦╚╦öĄ(sh©┤)▒ŖČÓĄ─╬─īW(xu©”)äō(chu©żng)ū„ĻĀ╬ķŻ¼Įø(j©®ng)│Żīæū„Ė„ŅÉ╬─īW(xu©”)ū„ŲĘš▀╔Ž░┘╚╦Ż¼ķgöÓ╔µ½CŠÄīæš▀Äū░┘╚╦Ż¼Å─ėūąĪ║ó═»ų┴ļŻ±¾╬╠╣½Ż¼Ė„─Ļ²gČ╬Č╝ėą─¼─¼Ė¹į┼š▀Ż¼├┐─Ļ╣½ķ_░l(f©Ī)▒Ēū„ŲĘ╔ŽŪ¦Ų¬Ż©╩ūŻ®Ż¼▀@╩Ūę╗ĘN╩«Ęų┐╔Ž▓Ą─Š░ė^┼cŠ░Ž¾Ż¼ę▓╩Ū┴ų┐hÜv╩Ę╔ŽÅ─╬┤ėą▀^Ą─╬─’L(f©źng)╩ó╩┬ĪŻ×ķī”▀@ę╗├└║├╩┬╬’ėą╦∙│½ōP║═╝żäŅŻ¼ęįé„║¾╚╦Ż¼Įø(j©®ng)╩ąą┬┬äųąą─Īó╩ą╬─┬ō(li©ón)Īó╩ąū„╝ęģf(xi©”)Ģ■ČÓĘĮ┼¼┴”▀\ū„Ż¼īóĖ„ĢrČ╬Ė„éĆīė├µėą┤·▒ĒąįĄ─╚Aš┬ģR╝»│╔ĪČ▓╝╣╚┴ųų▌ĪĘĪŻ╚ń╠½ąą╔Į├▄┴ųųą▒Ŗ°BŻ¼ęį╩Š╔Įę¶║═°QĪŻ
šfĄĮ╔Į궯¼╬ę╩ūŽ╚ŽļĄĮ┴╦╔Į═Ōų«ę¶Ż¼▒Ń╩Ū▀hį┌ĖŻĮ©╚╬╩Ī╬─┬ō(li©ón)Ė▒ų„Ž»Ą─ū„╝ęŚŅ╔┘║ŌŻ¼╦¹ūµ╝«┴ųų▌Ż¼ŲõĖĖ╩Ū1949─Ļ─ŽŽ┬Ė’├³Ė╔▓┐ĪŻ╬ęļmų┴Į±╬┤┼c╔┘║Ōų\├µŻ¼ģsį┌1995─Ļęč┼c╦¹ėą╬─īW(xu©”)Į╗═∙Ż¼╦¹į°╝─╬ęę╗▒Š╦¹įńŲ┌Ą─╬─╝»ĪČ╬„’L(f©źng)¬Ü▓ĮĪĘŻ¼║¾┐┤ĄĮ╦¹īæĄ─ĪČ╣╩Ól(xi©Īng)ų«┬├ĪĘĪŻ╬ęį°ėąĖąīæ▀^ę╗Ų¬ĪČėøų°╔┘║ŌŽļŲ─ŽŽ┬ĪĘŻ¼Į³─Ļ┐┤ĄĮ╔┘║Ōäō(chu©żng)ū„žS╩šŻ¼Ēæų`╚½ć°Ż¼×ķ╝ęÓl(xi©Īng)╠½ąą╔Įų«╚╦├}╬─ÜŌū▀│÷╚ń┤╦ėą│╔Š═ū„╝ęŻ¼ū„×ķ╣╩Ól(xi©Īng)╚╦ĖąĄĮ╩«Ęųą└╬┐ĪŻ
ĪĪĪĪ
šfĄĮ╔Į궯¼ėų▓╗─▄▓╗╠ß╝░╠ŲŠ²┼dĒśĪŻ╠Ųę└╔Į┐┐╔ĮŻ¼╦¹╚╦╦¹╬─Č╝╩Ū┤¾╔ĮB(y©Żng)ė²Č°│╔Ą─ĪŻ┤¾╔Į╣®æ¬(y©®ng)┴╦╦¹│õūŃĄ──╠╦«Ż¼╦¹▒Ńīæ┴╦įSČÓ┼c╔Į┼c╦«┼c╚╦Ą─╬─š┬ĪŻ┼dĒś│§╔µīæū„ĢrŻ¼╣ź▀^įŖĖĶļs╬─Ż¼Ųõ╔ó╬─ęčėą20─ĻĖ∙╗∙Ż¼Ųõ╬─ūų╣”┴”╦╝Žļ╦«£╩(zh©│n)Ż¼ęčĘŪę╗░ŃŠ│ĄžĪŻ╬ę¬qŲ½É█╦¹Ą─ĪČų┬┼«ā║Ģ°ĪĘŻ¼╬ęŲ½É█Ą─╩Ūę╗éĆšµūųŻ¼─ŪĘNšµ╝╚╩Ū╦¹×ķ╬─ų«šµĪóų«ŪķŻ¼ę▓╚┌╚ļ┴╦╠ņŽ┬ĖĖ─Ė×ķĖĖ×ķ─ĖĄ─ą─Ą─ŪķĪŻ▀@▒Ń╩Ūū„ŲĘĄ─╔ŅČ╚┼cÅVČ╚ĪŻŲõčįšZŪķŠ░Ż¼Į^▓╗╩Ū╚╬║╬ę╗éĆ╚╦┐╔ęįŠÄįņ│÷üĒĄ─Ż¼╩Ūšµą─šµŪķĄ─┴„┬ČĪŻæ¬(y©®ng)┴╦šµīŹ╩Ū╦ćąg(sh©┤)Ą─╔·├³ĪŻ╠Ų┼dĒś╩ŪéĆ║▄Š½├„ėąų„ęŖŻ¼ėų║▄Ģ■äØėŗ╬³╩šĄ─╚╦Ż¼╦¹Ą─ā╔▓┐╔ó╬─╝»Š═╚½╩Ūį┌╦¹Å─š■Ą─ķgŽČäØėŗ│÷üĒĄ─Ż¼╦¹Ą─ū„ŲĘČ╝ØB═Ėų°╦¹ī”╚╦ī”╩┬╬’Ą─šJ(r©©n)ūR║═╦╝┐╝ĪŻ
ĪĪĪĪ
Åł▄Ä£Y¤ßųįė┌╬─īW(xu©”)ę▓ėąą®─ĻŅ^┴╦Ż¼20╩└╝o(j©¼)80─Ļ┤·╦¹Š═╔ŽĪČ╔Į╬„┤¾īW(xu©”)ĪĘĄ─īæū„┐»╩┌░ÓŻ¼╦¹╩ų┐ņŻ¼īæ┴╦įSČÓ╝o(j©¼)īŹąįū„ŲĘĪŻųąķg×ķ╔·ėŗėą▀^┤ųųŲ║═└óī”╬─ūųŻ¼╬ęį°Ž“╦¹æ“ĘQ▀^Ī░─Ńéā▀@ą®└Žė═ūėĪ▒Ż¼╦¹×ķų«ę╗ą”ĪŻ╦¹Ą─ĪČ╗ž═¹æ¶┐┌ĪĘĘŪ│Żėą╠ž╔½Ż¼ø]ėąėH╔ĒĮø(j©®ng)ÜvĖą╩▄╔Ņ┐╠Ą─╚╦Ż¼Į^ī”šf▓╗│÷─ŪśėĄ─įÆīæ▓╗│÷─Ūśė╔ŅÕõĄ─╬─ĪŻę╗éĆæ¶┐┌Ę┤ė│┴╦─Ūę╗ĘNĢr┤·Ż¼ę╗éĆæ¶┐┌öóīæ┴╦ę╗éĆ╚╦Ą─┐▓┐└┼c│┴ĖĪŻ¼▀@Š═╩Ūū„ŲĘĄ─ārųĄĪŻū„ŲĘ┐é▀Ć╩Ūæ¬(y©®ng)įōī”╚╦ī”╔ńĢ■Ų³cū„ė├Ż¼▓┼ėą▒žę¬┤µį┌Ą─ĪŻ║├ū„ŲĘ═∙═∙īæĄ─Š═╩ŪśOŲĮ│ŻĄ─╩┬ĪŻ╚╦╚╦ė¹šfėųø]šf│÷üĒĄ─╩┬Ż¼▀@śė▓┼Ģ■ėą╣▓°QĪŻ╔·ŠÄė▓įņĄ─ļxŲµ¢|╬„Ż¼├═ę╗┐┤ę▓Ģ■ćś╚╦ę╗┤¾╠°Ż¼╝Üę╗Į└Š═┴Ņ╚╦ū„ćI┴╦ĪŻ╬ę│§┐┤ĪČ╗ž═¹æ¶┐┌ĪĘĄĮĮY(ji©”)╬▓ĢrŻ¼į°Įø(j©®ng)┼─▀^░ĖŻ¼ėąę╗ŠõįÆīæĮ^┴╦Ż¼─Ūšµ╩Ū«ŗ²ł³cŠ”’wüĒų«╣PŻ¼×ķ▀@ę╗╣PŻ¼Å─╦¹ĮĪēčĄĮąĪ╝▓╩¦šZŻ¼ā╔─Ļųą╬ęį°ČÓ┤╬Ž“╦¹╠ߥĮ▓ó╩ŠęŌķ_═µą”Īó┘uĻP(gu©Īn)ūėŻ¼▀@└’¤oąĶ┘śčįŻ¼├„č█╚╦ę╗┐┤▒Ńų¬ĪŻ
ĪĪĪĪ
įŁŠG╔½ę▓ėąĮ³20─ĻĄ─äō(chu©żng)ū„Įø(j©®ng)ÜvŻ¼╦¹│§Ų┌▀MąąĄ─äō(chu©żng)ū„ČÓ┼c╦¹Ą─Į╠ė²╔·č─ėąĻP(gu©Īn)Ż¼Å─ė^▓ņĪó蹊┐╔·╗Ņ│÷░l(f©Ī)Ż¼īæ┴╦ę╗┤¾┼·Ä¤╔·ėčŪķ║═ā║═»╬─īW(xu©”)ū„ŲĘŻ¼╚ńĪČŚŅŽ╚╔·ĪĘĪóĪČŪ’╠ņĄĮ┴╦ĪĘĪóĪČ═¼ū└Ą─░ļĮžŃU╣PĪĘĪóĪČśŪ╠▌▀ģ╔ŽĪĘĄ╚Ż¼šZčį┴„Ģ│Ż¼═»ą─ų╔╚ż║▄ØŌŻ¼Įo╚╦ŪÕą┬Ž“╔ŽĄ─åóĄŽĮ╠šdĪŻ║¾Øōą─Į╠äš(w©┤)Ż¼¤oķg▀Mąą╣PĖ¹ĪŻą┬ū„ĪČ└Ž╝ę╦«║ėĪĘŻ¼ęč▀h▓╗╩Ū╦¹─Ūį┤ūį╔·╗ŅĄ─Ūķ╚ż░╗╚╗’L(f©źng)Ė±ĪŻ
ĪĪĪĪ
äóąg(sh©┤)ŽŃ╩ŪéĆ║▄╔Ųė┌ė^▓ņ╔·╗Ņėųėą¬Ü╠žęŖĄžĄ─┼«ąįŻ¼▀@ę▓╩ŪĖ„ūįĄ─╚╦╔·Ą└┬ĘįņŠ═Ą─ĪŻ╦²ęčĮø(j©®ng)│÷┴╦ā╔▒Š║▄ėąė░ĒæĄ─įŖ╝»Ż¼įuįŖ╚╦šf╦²╩Ūį┌ė├ūį╝║Ą─╦╝ŠSīæ╔·╗ŅŻ¼įŖęŌ╔ŅĪóņ`ąį┤¾ĪŻę╗░ŃČ╝šJ(r©©n)×ķ╦²╩ŪéƬÜ╠žĄ─įŖąį╚╦ĪŻĄ½╬ęėXĄ├╦²Ą─╔ó╬─ę▓║▄Š½ĄĮŻ¼ęį╗Ņņ`Ą─╝Ü╣Ø(ji©”)ū▓ō¶ūxš▀Ą─Ėąų¬Ż¼ėąę╗ĘNōõ▒ŪĄ─Ól(xi©Īng)═┴ĒŹ╬Č║═▓╗┴╦Ą─ŪķĮzĪŻ╬ęī”╦²Ą─ĪČ╬ęÉ█ČĪŽŃ╗©ĪĘį°£\┬¬Ąž³cįu▀^ā╔ŠõŻ¼ČÓ─Ļ║¾╬ęŽļŲüĒ─Ū▀Ć╩ŪŲ¬║├╔ó╬─ĪŻ
ĪĪĪĪ
╔ĮŪÓĄ─Č╠╔ó╬─ĘŪ│ŻūóęŌ╩┬╬’ā╚(n©©i)į┌Ą─ÜŌĒŹŻ¼╬─ūųę▓║▄ųvŠ┐Š½¤ÆŻ¼ūųį~║¼ąŅŻ¼ę▓ėą³cōõ╦ĘĄ─ĖąėXŻ¼ėą╦╝┐╝┐šķgŻ¼Č°Ūę║▄┤¾ĪŻ
═¼śėūóųžšZčį╣”┴”Ą─ĖĄ├¶Ż¼įń─ĻČÓęįÓl(xi©Īng)╩┬īæīŹęŖķLŻ¼║¾╣ź▀^╔ó╬─įŖąĪšfę╗ŅÉĪŻū„▀^ČÓĘNćLįć║¾Ż¼Į³─ĻČ©Ė±│╔¼F(xi©żn)į┌Ą─╬─š┬śė╩ĮĪŻĪČĖĖėHĄ─¹£ūėĪĘėą╠ž╔½Ż¼ę²Ų▓╗ąĪĄ─Ę┤ĒæĪŻ
ĪĪĪĪ
ŚŅųŠėŅ╩ŪéĆ╩«Ęųā╚(n©©i)Ž“▓╗ÅłōPĄ─╚╦Ż¼╦¹į┌─¼─¼Ąžūó─┐ų°╩└╩┬Ż¼ė^▓ņų°╔Ē▀ģ╚╦Ż¼╦¹Ą─╬─╣P║▄╝Ü─üŻ¼ČÓÅ─│Ż╩┬ųąķ_Š“╚╦ąį┼c╔ńĢ■Ą─▒Š┘|(zh©¼)Ż¼╦¹15─ĻŪ░īæĄ─┤“╣ż╔·╗ŅŻ¼Äū┤╬ėą╚╦═¼╬ęšfŽļ┼─│╔ļŖęĢäĪŻ¼╦¹Ą─ąĪšfĪČ╗╝tĄ─č“├½╔└ĪĘį┌ĪČ╬─į┤ĪĘ░l(f©Ī)▒ĒŻ¼ėųę²ŲĘ┤ĒæŻ¼╬ęį°×ķŲõįu³c┴╦ÄūŠõĪŻ
ĪĪĪĪ
äóÅV╝¬╩ŪéĆĄžĄ└Ą─▐r(n©«ng)├±Ż¼ę▓╩ŪéĆ║▄ėą╬“ąįėą╝żŪķĄ─įŖ╚╦ĪŻ╬ę│Ż│Ż▓╗ĮŌĄžå¢╦¹Ż¼─Ńš¹─Ļ─_▓╚ų°═┴ĄžŻ¼├µī”ų°Ūf╝┌Ż¼─Ūą®Č╝╩ŪīŹĄ─Ż¼─Ń──üĒ─Ū├┤ČÓ╚╝¤²Ą─įŖŠõŻ┐╩Ū──ę╗ųĻ║╠├ńŻ¼──ę╗┴ŻĘNūė╣┤Ų─ŃĘ┼┐vĄ─╝żŪķŻ┐╦¹╩ŪéĆšµš²Ą─å╬Ė╔š▀Ż¼ėųę╗³c▓╗┬õ╬ķ▓╗┬õ╠ūĪŻ╬ę│Ż═¼╦¹æ“═µĪ░─Ń╩ŪéĆ▓Ņę╗³cø]│╔īó▄ŖĄ─įŖ╚╦Ī▒Š═╦¹īæ│÷Ą─įSČÓįŖŲ¬ųąĄ─įŖĘÕĄ─Øq┴”┐┤Ż¼▓╗¤o├╔ī”Ą─ĪŻŽ¾▀@Ī░┴ųžSõXļŖ╚╦Ī▒ųą╦¹╦∙ćŖ│÷Ą──Ūą®╬─ūųĪŻ
ĪĪĪĪ
░ū┼dč┼Ż¼ūµ╝«─ŽĻ¢Ż¼╩ŪĮ³─ĻüĒį┌┴ųų▌▀@Ų¼═┴Ąž╔Ž├░│÷üĒĄ─ę╗éĆĮM║Ž╬─ūųĄ─┼«ÅŖ╚╦Ż¼╦²┤¾Ė┼╩Ū░čÅ──ŽĻ¢┼P²łš┤üĒĄ─ņ`ąįŻ¼┼c╠½ąą┤¾╔ĮĄ─╔Ņ║±╚Ó│╔┴╦ę╗¾wŻ¼╦²Ą─╬─ūų’@Ą├╝╚ņ`ąŃėųŪfųžĪŻ╬ęį°Įø(j©®ng)╣╬─┐ŽÓ┐┤▀^╦²─ŪéĆĪČØO╩┬ĪĘŻ¼ūŅ│§╔§ų┴▓╗ŽÓą┼╩Ū│÷ūįę╗éĆąĪ┼«ūėĄ─╩ųĪŻĪČØO╩┬ĪĘķ_Ų¬─Ū╚ńįŖ╚ń«ŗĄ─Š│ĮńŻ¼šµ┐╔ęįšf╩ŪīæĄĮ┴╦Į^╠ÄŻ¼╠½ėą╔±ĒŹ┴╦Ż¼ę╗ą®ęŌŠ│ū„┼╔Äū║§┐╔┼c┴╬╚AĖĶĄ─╔ó╬─ęŌ╠NüĒµŪ├└ĪŻĄ½╩ŪĮėŽ┬üĒŻ¼ŖA╔·┴╦³cŻ¼╦Ų╩Ū│÷ūįČ■╚╦╩ųŻ¼╗“ķgĖ¶ĪóķgöÓĢrķg╠½Š├Ż¼ÜŌĒŹø]▀B║├ĪŻĪ░▀@└’ę¬╩ūŽ╚Į╗┤·ę╗Ž┬╬ęĪ▒Ž±ę╗ēK╩»Ņ^įę▀M┴╦├└├ŅĄ─║■├µųąŻ¼═©Ų¬ėąę╗łF║├├µø]╚Ó║├Ą─ĖąėXĪŻ▒M╣▄╚ń┤╦Ż¼ĪČØO╩┬ĪĘ╚į▓╗╩¦×ķę╗Ų¬╬─ūųā×(y©Łu)├└Ż¼ęŌŠ│╔ŅÕõĄ─║├ū„ŲĘŻ¼─═ūxėąėÓ╬ČĪŻ
ĪĪĪĪ
äóä”└źĄ─ĪČ╔ĮėĻĪĘį┌š▄└ĒĪó╔±ÜŌ╔Ž¬ÜėąęŖĄž▀M┴╦ę╗éĆŽ’Ą└ĪŻ╦Ųį┌╝ā┤ŌĄžīæ╔Įīæ╣╚īæįŲņFĪŻ▒M╣▄ėąą®╩Ū│Ż╚╦ļyęįūxČ«╦¹▒ŠęŌŻ¼Ą½╩ŪĘN│¼├ōĄ─Š│ĮńĪŻ▀@║═╦¹įńŲ┌īæĄ─╔·╗Ņ╗»ąĪšf╔ó╬─Ż¼╚ńĪČ╦═─╠╚╦ĪĘĄ╚Ą─┴óęŌ▀x▓─╩Ū┤¾▓╗ŽÓ═¼Ą─ĪŻ
ĪĪĪĪ
Į³─ĻüĒŻ¼│Ż┐ĪĮ▄Äū║§▒╗┴ųų▌╬─Įń▀z═³ĪŻŲõīŹ╦¹¤ßÉ█╬─īW(xu©”)Ż¼░Ąųąīæū„║▄įńĪŻ20╩└╝o(j©¼)70─Ļ┤·ųąŲ┌Ż¼╦¹Š═“Tų°ŲŲ┼fūįąą▄ćŻ¼ū▀Äū╩«└’╔Į┬ĘŻ¼ĄĮ╬ę└Ž╝ęĪ░šłĮ╠Ī▒ĪŻ╚ńīŹšfŻ¼╦¹▓╗▀^╩Ū─Į├¹ĪČ╠½ąąųŠĪĘĪŻ╦¹╣®┬Üą┬┬ä▓┐ķTĮ³20─ĻŻ¼īæ┴╦ę╗┤¾┼·║▄ėą╬─īW(xu©”)╬ČĄ─═©ėŹĪó╔ó╬─Ż¼╚ńĪČ▀xĢr╣ŌĪĘĪóĪČ═├×ķ├ĮĪĘĪóĪČ┌sĢ■ĪĘĪŁĪŁČ╝ęŖųTĪČ╚╦├±╚šł¾ĪĘĪóĪČą┬ė^▓ņĪĘĄ╚┤¾ł¾┐»ĪŻ╦¹įńŲ┌ųž╬─║¾üĒųžš■Ż¼─Xūėņ`╗ŅŻ¼╔Ųī”æ¬(y©®ng)Ż¼ų▒ĄĮļx┬Ü▓┼ė¹ųž▓┘┼fśI(y©©)ĪŻ▒Š╝»▀x╦¹ę╗Ų¬ĪČŠ╚═▐ĪĘŻ¼ā╔─ĻŪ░│§ĖÕ╝┤ūī╬ę┐┤▀^Ż¼ėXĄ├ėą³c═Ō╔¹┤“¤¶╗\ĪŻ╬ęį°┤ų▒®Ąžįę┴╦Äū░¶Ż¼║├į┌╦¹ėąĒgąįŻ¼Įø(j©®ng)Ą├╚²┤uā╔═▀ĪŻĮ±ėų─├üĒŻ¼╬ęį┘┐┤ĢrŻ¼ėą³cęŌ╦╝Īó│÷ą┬ĪŻęŌ╦╝į┌ĮY(ji©”)╬▓Ż¼ėą³cÜW║Ó└¹Č╠Ų¬ĮY(ji©”)śŗ(g©░u)Ą─╬ČĄ└ĪŻę╗Ų¬╬─š┬╝┤╩╣ų╗ėąę╗³cą┬ęŌŻ¼ę╗³c╦ćąg(sh©┤)ę▓ųĄĄ├šõęĢŻ¼ę“×ķ▀@ę╗³cģs╩ŪüĒų«▓╗ęūĄ─ĪŻ
ĪĪĪĪ
▒M╣▄ėąĄ─╚╦īæū„Ģrķg▓╗Č╠Ż¼ę▓īæ┴╦▓╗╔┘Ż¼Ą½ė├╝āš²╬─īW(xu©”)äō(chu©żng)ū„│▀Č╚üĒ┴┐Ż¼▀Ćėą║▄┤¾ŠÓļxŻ¼│õŲõ┴┐ų╗─▄╦Ń═©╦ūūx╬’ĪŻę╗éĆū„š▀╚ń╣¹ķLŲ┌═Ż┴¶į┌ūįęį×ķ╩ŪŻ¼─ŪŠ══Ļ┴╦Ż¼šf├„╦¹ø]▀M▓ĮŻ¼╗“š▀Ė∙▒ŠŠ═ø]├■ūĪ╬─īW(xu©”)äō(chu©żng)ū„Ą─ķTÖæĪŻų╗ėąį§├┤┐┤ūį╝║Ą─ū„ŲĘ├½▓Īę▓▓╗╔┘Ż¼▓┼╦Ń░°╔Ž┴╦╬─īW(xu©”)Ą─▀ģŻ¼šµš²ėą╣”┴”ę²Ų╣▓°QĄ─║├ū„ŲĘŻ¼Į^▓╗╩Ū┐┐Ī░ūįū„┬ö├„Ī▒║═Ī░ūņė▓Ī▒Ą─ĪŻ
ĪĪĪĪ
ę“×ķč█Ė▀╩ųĄ═╩Ūę╗ĘN═©▓ĪŻ¼Ī░╩║┐╦└╔ų╗šf╦¹║óŽŃĪ▒ėą▀zé„ĪŻū÷╚╦č█▓╗Ė▀▓╗ąąŻ¼ø]└ĒŽļŻ╗ų╗č█Ė▀╩ų▓╗ū÷╗“ū÷▓╗ĄĮ╩Ū╠Äę▓▓╗ąąĪŻėąą®╚╦šfŲüĒ╚ń’L(f©źng)╦ŲėĻŻ¼║├Ž±╦¹╔ČČ╝Č«Ż¼▀@╩ŪšµČ«å߯┐ę▓ėą╚╦░č╬─īW(xu©”)šfĄ├║▄╔±├žŻ¼║▄ą■,Ž±ąĪŲĘ└’Ą─╦╬ĄżĄżą■│÷Ģ°Ż¼ŲõīŹ╬─īW(xu©”)┼c╩└ķgĖ„ąąĖ„śI(y©©)ėąįSČÓ╣▓═¼╠Ä,╚f╬’ę╗└Ē,╚╬║╬╩┬Ūķę¬│╔╣”ę¬▀_ĄĮę╗Č©Ė▀Č╚Č╝▓╗╚▌ęū,ę╗─_Å─═┴└’╠▀│÷üĒéĆĮĖ“¾ĪĄ─Ė┼┬╩Ą╚ė┌┴ŃĪŻ╦«ŲĮ╩ŪĘ┼į┌╚f▒Ŗ▓┘┐vĄ─╠ņŲĮ╔Ž│ė│÷üĒĄ─ĪŻ
ĪĪĪĪ
═§║Ļ├±ę▓╩Ū└Žę╗▓ńīæ╝ęŻ¼įńŲ┌ī”╬─īW(xu©”)ĘŪ│Żō┤É█Ż¼20╩└╝o(j©¼)Ų▀░╦╩«─Ļ┤·Ż¼Š═Ū┌Ŗ^╣PĖ¹Ż¼Ųõū„ŲĘėą─┐╣▓Č├ĪŻ╦¹īæ╔ó╬─įŖĖĶė╬ėøŻ¼║¾Š½┴”ė├į┌ŠÄūļ╔ŽĪŻ╦¹Ą─┤¾ū„×ķį┌╩ĘųŠĪŻė╚Ųõ╩Ū╝tŲņŪ■ųŠ,╣ż│╠║Ų┤¾Ż¼═Ļ│╔║▄▓╗╚▌ęū, ĘŪę╗░Ń╚╦┴”╦∙─▄╝░ĪŻ▒M╣▄ę▓ėąą®ŪĘ╚▒,╔§ų┴éĆäe╚╦ėą▓╗═¼┐┤Ę©,ėą³cĄ╬▓ŅÕe║═╝ä┬Č─Ū╩Ūļy├ŌĄ─ĪŻ
ĪĪĪĪ
ŚŅėŠĮŁį┌įŖ║ŻųąĮ■┼▌┴╦ČÓ─ĻŻ¼╦¹įńŲ┌īæĄ─įŖ║▄śŃīŹĪó║▄╝āā¶Īóę▓║▄ėąņ`ąįŻ¼ėą┴╦ūį╝║Ą─’L(f©źng)Ė±ĪŻ║¾ėų╣ź▀^ąĪšf╔ó╬─Ż¼ę▓┤“╦Ń▀^īæą®Ģr╔ąčįŪķĪŻĄ½╚²ĘĮ├µČ╝╬┤▀_ĄĮæ¬(y©®ng)ėąĄ─Ė▀Č╚Ż¼╦∙╝»ų«įŖ▀h▓╗─▄┤·▒Ē╦¹Ą─╬─ūų╦«ŲĮĪŻ╬ę┐┤╦¹▀Ć╠N▓žėą║▄┤¾Ą─äō(chu©żng)ū„Øō┴”Ż¼ø]ėą╚½┴”ęįĖ░▒│╦«ę╗æ(zh©żn)Üó│÷ę╗Ślč¬┬ĘŻ¼ę“×ķ╦¹šŲ╬šĄ─ę¬╦ž▓╗╔┘Ż¼į°ā╔▀MĪ░¶öį║Ī▒čąūxŻ¼ī”įŖėąČÓĘĮ├µćLįć┼c╠Į╦„Ż¼ĻP(gu©Īn)µI╩Ūö[▓╗├ō╩└╩┬ū¾ėęŻ¼╬┤─▄ņoą─īŻą─Ż¼ę╗╣╔ū„ÜŌšę£╩(zh©│n)═╗ŲŲ┐┌ĪŻ╦¹ėą─▄┴┐Ż¼┼╬─▄įń╚š┐┤ĄĮ╦¹▒¼š©ąįĄ─┬Ģė░ĪŻ
ĪĪĪĪ
┼cėŠĮŁ═¼▓ĮĄ─▀ĆėąéĆĖ▀├„é}Ż¼Įø(j©®ng)ČÓ─Ļ─źŠÜŻ¼į┌Ól(xi©Īng)═┴įŖ╔Žęčėąūį╝║Ą─┬ĘöĄ(sh©┤)Ż¼äō(chu©żng)ū„╝żŪķę▓š²═·╩óĢrŻ¼ė÷ĄĮ▓╗£yĪŻ╦¹į┌Ól(xi©Īng)š■Ė«╣żū„Į³20─ĻŻ¼ėų╚╬▐k╣½╩ęų„╚╬ČÓ─ĻŻ¼Š╣▓╗├”░čūį╝║▐D(zhu©Żn)š²Ż¼║÷ę╗Ģrę╗┬╔╚½ŪÕ┼RĢr╣żĢrŻ¼▒Ń▒╗ŪÕ═╦Ż¼▒Ń╔±╔Ēā╔é¹Ż¼Č╚╚šŲDļyŻ¼║╬čįįŖ┼dŻ┐▓╗▀^╬ęŪęšJ(r©©n)Č©Ż¼Ė▀╩Ž├„é}ą─Ąū╝╚ęčĘNŽ┬ę╗┐├’¢ØMĄ─Ī░įŖĘNĪ▒Ż¼▀@ĘNūė┐éĢ■ėąŲŲ═┴Č°│÷Īóķ_╗©ĮY(ji©”)╣¹Ą─Ģr║“ĪŻ
ĪĪĪĪ
╔ą┤õĘ╝▒Š╩Ūę╗éĆ▓žį┌Į╠╩ę└’Ą─┼«ąįŻ¼ė╔ė┌╬─ą─Ą─šą╚ŪØLäėŻ¼į┌┴ųų▌╬─Įńęč│§┬Čšµ╚▌Ż¼╦²īæįŖīæ╔ó╬─ę▓īææ“Ū·Ż¼╔ó╬─ųąČÓę²Įø(j©®ng)ō■(j©┤)Ąõ╣┼įŖį~Ż¼╬─╣PęÄ(gu©®)ĘČŻ¼ėą³cīW(xu©”)į║┼╔╝▄ä▌Ż¼šZčį┴„Ģ│Ż¼Ī░ąė╗©ų«ĒŹĪ▒ų╗─▄╦Ńįć╣PŻ¼šµš²ėąĘ▌┴┐ķW╣ŌĄ─¢|╬„▀Ćæ¬(y©®ng)įōį┌║¾▀ģĪŻ
ĪĪĪĪ
╣∙ė±’L(f©źng)╩ŪĮ³─Ļ│÷¼F(xi©żn)Ą─ę╗éĆ╬─īW(xu©”)ą┬ąŃŻ¼╦²╚╦╦²╬─Č╝║▄╝āśŃį·īŹŻ¼šJ(r©©n)šµū÷╚╦Ż¼ū÷╩┬Ż¼▀hļx╣”└¹ĪŻ╦²Ą─╦╝Žļ├¶õJŻ¼ė^▓ņ╩┬╬’Š½ĄĮŻ¼╬─ūųę▓ėą╣”┴”Ż¼Ą½╩Ū╦²ūįęčīæū„ŲĘ║▄╔┘,Äū║§╩Ū░č╚½▓┐ą─č¬ė├į┌┴╦×ķäe╚╦ū„╝▐ę┬Ż¼└¹ė├Ī░┴ųų▌Ī▒╔Žķ_▒┘Ą──ŪąĪąĪę╗ēKł@ĄžĪŻą┴Ū┌Ąž×ķ├┐ę╗┐├║╠├ń┼Ó═┴×ó╦«Ż¼į┌ėą³cĖĪį’Ą─│▒┴„ųąŻ¼ę╗éĆ║▄─Ļ▌pĄ─┼«ūė─▄ėą▀@ę╗ĘNŲĘĖ±╩Ū┴Ņ╚╦Š┤┼ÕĄ─ĪŻ
ĪĪĪĪ
ŚŅزŻ¼ī┘┴ųų▌╬─īW(xu©”)ĮńūŅ─Ļ▌pĄ─ę╗┤·Ż¼─Ļ▌p▒ŃŠ▀éõ║▄ČÓā×(y©Łu)ä▌Ż¼╩ūŽ╚╩Ū╬┤üĒĄ─╚šūė║▄ķLŻ¼ėąīÆÅVĄ─░l(f©Ī)š╣Ŗ^ČĘ┐šķgĪŻ─Ļ▌pŻ¼▒ŃĢr┤·ęŌūRÅŖŻ¼▒ŃŪķŠw╗Ņ▄SŻ¼ŽļŽ¾┴”žSĖ╗Ż¼ęū│÷Ųµ│÷ą┬ĪŻųąć°įńėąĪ░└Ž▓╗┐┤╚²ć°╔┘▓╗┐┤╬„ė╬Ī▒ų«šfĪŻŚŅزĄ─╬─ūų┴„Ģ│Ż¼ėą¬ÜĄĮĄ─╣”┴”┼c╠ž╔½Ż¼╚ńĪČ╔±╝╝ĪĘ╩ŪČ╠Ų¬ąĪšfę▓Ž±įóčįŻ¼╦¹└¹ė├╔±ŲµÄ¦³c╗├ėXĄ─ŽļŽ¾┼c╔├ūāĄ─śŗ(g©░u)╦╝╩ųĘ©Ż¼└¹ė├Ė„ĘNäė╬’Ą─╠žš„┼c╣į╗¼Ż¼Įę╩Šų°╚╦ķgĄ─žØ└Ę┼c│¾É║Ż¼ėą╚ż┐╔ūxĪŻ▀B═¼ĪČČŠ╔▀ĪĘĪóĪČįĮ¬zĪĘĄ╚Č╝╩ŪŲµ╦╝├ŅŽļĦų°įóčį╩Į╔½▓╩Ż¼Ą½ėųČÓ╚ń╔Ē▀ģ╩┬Ż¼┐╔ė|ėų┐╔├■ĪŻ▀@╩Ū╦ćąg(sh©┤)Ż¼▀@╩Ū╦¹Øōą─ū┴─ź│÷üĒĄ─Ż¼«ö(d©Īng)╚╗ę▓ļy├Ō╩▄╦¹åó░l(f©Ī)┼cĖą╚ŠĪŻ▀@ĘNęÓ╗├ęÓīŹĄ─Š│ĀŅŻ¼ą╬│╔┴╦ŚŅزČ╠Ų¬Ą─╠ž╔½Ż¼ę╗ĘN╠ū┬ĘŻ¼╣”Ę“ĄĮ┤╦Ąž▓Į▓╗╚▌ęūŻ¼ų╗╩Ū│╔┴╦╠ūŻ¼Š═ļy├Ōėą╦Ųį°ŽÓūR╠ÄŻ¼╚¶į┘Ž“╔Ņ╠Äķ_Š“ķ_Š“Ż¼į┘Å─╠ū┬Ęųąū▀│÷üĒĪŁĪŁ
ĪĪĪĪ
╣∙Ū’Ššį┌Ę▒├”Ą─╣½░▓æ(zh©żn)ŠĆŻ¼ęį╦²Ą─ę╗╣╔š²┴xų«ÜŌŻ¼Ė▀Č╚Ą─╔ńĢ■ž¤(z©”)╚╬ĖąŻ¼æčų°╝āØŹ┴╝╔Ųų«ą─Ż¼ė├╩ųųąų«╣PŻ¼ī”┤²Õe╩¦Ż¼═ņŠ╚ņ`╗ĻĪŻÅ─ę╗éƬÜ╠žĄ─ęĢĮŪŻ¼öóīæŠÄ▌ŗ▀^ę╗┤¾┼·¼F(xi©żn)īŹąį║▄ÅŖĄ─╬─ĖÕŻ¼ī”╔ńĢ■ī”┤¾▒ŖęųÉ║ōP╔ŲŻ¼╩šĄĮ▀^║▄║├Ą─ą¦╣¹ĪŻ╝»ųą╦∙╩š▀@Ų¬Ż¼āHāH╩Ū╦²Å─╬─Ą─ę╗éĆąĪąĪĄ─é╚(c©©)├µĪŻė╚Ųõ╩Ū╦²ų„│ųĪČ┴ųų▌Š»ē»ĪĘČÓ─ĻŻ¼ŠÄīæ┴╦┤¾┴┐░┘ąšŽ▓┬äśĘęŖĄ─Š»ńŖ╣Ø(ji©”)─┐Ż¼Įo╚╦╔Ņ┐╠Ą─Į╠šdĪŻ
ĪĪĪĪ
┴ųų▌ėąę╗┤¾┼·Å─╔·╗Ņ│÷░l(f©Ī)Ż¼öóīæÓl(xi©Īng)ŪķÓl(xi©Īng)╩┬ėHŪķėčŪķĄ─īæ╝ęŻ¼║▄─═ūxŻ¼║▄ėąÓl(xi©Īng)═┴╚╦Ūķ╬ČĪŻ╚ńŚŅė±¢|Č╠Č╠Äū─Ļųą░l(f©Ī)▒Ē┴╦Äū╩«Ų¬▀@śėĄ─ū„ŲĘŻ¼’@╩Š│÷ę╗ĘNÅŖä┼Ą─äō(chu©żng)ū„īŹ┴”Ż¼▀@╩Ū╩«Ęų┐╔Ž▓Ą─╩š½@ĪŻį┘╚ń╦∙▀x║┬╚ńš┬Ą─ÄūŲ¬ū„ŲĘŻ¼ę▓╚½üĒūį╔·╗ŅĪŻ╚ńŲ¹Ū“Īó┘užiĪóĮą╗Ļā║Ą╚ĪŻų╗ę¬ū„š▀ėą┴╦╔Ņ║±Ą─╔·╗ŅĄū╠N╝┤▒Ń╩Ū░l(f©Ī)ō]ŽļŽ¾│÷üĒĄ─Ūķ╣Ø(ji©”)╝Ü╣Ø(ji©”)Ż¼ę▓╩ŪšµīŹ┐╔ą┼Ą─ĪŻę“×ķ╦³ėąįŁ╩╝Ą─╔·╗ŅÜŌŽó║═├±ķg╬Čā║ĪŻ▀@╩Ū┐╔Ž▓Ą─ķ_Č╦Ż¼ę“×ķšµīŹ╩Ū╦ćąg(sh©┤)Ą─╔·├³Ż¼Ą½šµīŹėųĮ^ī”▓╗Ą╚ė┌╦ćąg(sh©┤)ĪŻū„ŲĘ’@Ą├ŲĮīŹ┴╦ą®Ż¼▀ĆąĶę¬╠ß¤ÆŻ¼ūźĄĮ┤¾³cĄ─ÜŌŻ¼╔Ņ³cĄ─ņ`Ż¼▓┼Ģ■ėąš╚╦ą─ņķĄ─ķW╣Ō╠ÄĪŻ
ĪĪĪĪ
╣∙į÷╝¬ę▓ūóęŌĄĮ┴╦ė^▓ņ╔·╗ŅŻ¼ėøæø╔·╗ŅŻ¼Ūęį┌ė├ę╗ą®╣┼į~╣┼ĒŹųŲįņę╗ĘNŠ│Ž¾Ż¼▀@ą®Č╝╩Ū╬─īW(xu©”)ųąĄ─╗∙▒Š╣”Ż¼╚ńąĪ║ėŻ¼╠O╣¹Ż¼°Bā║ĪóŚŚśõĪóąĪ▓▌╠ĮŅ^╠Į─XĄ╚Č╝×ķ╦³éā┘xė┌┴╦ņ`ąįŻ¼╗Ņ┴╦ŻĪĄ½ėąą®į~┼cÜŌĘš╩Ūʱ▓╗╠½║═ųCŻ¼╚ńõĮę┬┼«Īó╠į▓╦ŗDŻ╗╬ęÉ█▀@ąĪ║ėŻ¼×ķīżŲõį┤Ż¼ę“╔Į┬ĘŲķŹńėųū„┴TĪŻ╬─ūų▀ĆėąŠ½¤ÆėÓĄžĪŻ╚ńĮY(ji©”)╬▓ų┴─©▓╗Ą¶ō]▓╗╚źŻ¼ęčČÓ├┤═Ļš¹Ż¼Ūę×ķūxš▀┴¶Ž┬├└║├Č°═’Ž¦Ą─ŽļŽ¾┐šķgŻ¼║╬▒žĪŁĪŁ└Ņ║Ż│»Ā┐┼Ż╗©īæĄ├ėąą┬ęŌĪŻ
ĪĪĪĪ
äóŃy╚½ąų═Ē─ĻŖ^╣PŻ¼╩«Ęų┐╔Ž▓┐╔┘RŻ¼Ūę¤o╦Į▓╗łD╦∙ł¾Ż¼ī”╬─š┬ŲĘ╬╗ć└(y©ón)Ū¾Ż¼ĪČ³S╗Ķ¤oŽ▐║├ĪĘųąŻ¼īæĄĮ┤░║Ž┤░ķ_▀@ę╗╝Ü╣Ø(ji©”)ėąįŖęŌČÓĖ╗╔±ĒŹŻ¼ī”╔·╗Ņī”╚╦╔·ø]ėą╔Ņ┐╠¾w╬Čū┴─źĄ─╚╦Ż¼Į^ī”║¶▓╗│÷╚ń┤╦čįį~ĪŻ
ĪĪĪĪ
╬─š┬├Ņį┌Š½╚AŻ¼│Ż│Żę╗ŠõįÆę╗éĆäėū„Ż¼▒Ń«ŗ²ł³cŠ”Ż¼┴Ņ╚╦š║│▓╗═³Ż¼╬õŲĮ║ŻĪČĘųį┬’×ĪĘųąĄ──Ūę╗č└į┬’ׯ╗║┬╚ńš┬╬─ųąĄ─Ż║šŠĄ─ĻĀ┤ų┴╦ĪŻ╣∙į÷╝¬ąĪ║ėŪ─Ū─Ąž░l(f©Ī)ĖŻ┴╦ĪŁĪŁÅ─╔·╗ŅųąćŖ═┬│÷üĒĄ─čįšZŻ¼╩ŪūŅą╬Ž¾ūŅ├└¹ÉĄ─Ż¼ę╗ŠõĄų▀^Ę║Ę║ĄžĮŌšfę╗░┘ŠõŻ¼ĖŃ╬─īW(xu©”)Ż¼Š═ę¬īW(xu©”)Ģ■ųŲįņ▀@ĘNšZčįŻ¼į┌ÅV┤¾░┘ąšųąōõūĮ▀@ĘNšZčįŻ¼šZčį╩Ū╬─īW(xu©”)Ą─╗∙ĄA(ch©│)ĪŻ
└Žę╗▓ńĄ─īæ╝ęųąŻ¼▀ĆėąéĆ║┬Ēś▓┼ĪŻ╦¹╩ŪéĆČÓ├µ╩ųŻ¼Äū║§╩▓├┤śėĄ─╬─¾w╬─ūųČ╝īæŻ¼╦╝Žļ╠žĮŌĘ┼Ż¼╬ęį°æ“ĘQ╦¹╚²┐ņŻ¼ūņ┐ņ═╚┐ņ─Xūė┐ņŻ¼║¾üĒ▀@╚²┐ņ▒╗╣½šJ(r©©n)ĪŻĄ½╦¹īæĄ├ėą╔·╗Ņ╬Čā║Ą─Ż¼’@╩Š╬─ūų╦«ŲĮĄ─▀Ć╩Ū─Ūą®ā║ĢrĄ─Ól(xi©Īng)ķg╩┬Īóš┤ų°¢|ꔎ┬Ūf─Ó═┴¤¤╗Ą─ā║┼«ŪķĪŻ╚ńĪČ¹£ĮšČŌĪĘĪČ▓±╗ČčĪĘĪČĖ╔╝ZĪĘĄ╚ĪŻ
ĪĪĪĪ
╣∙▓╝╦┤╩ŪéĆ╩«ĘųŪ┌┐ņĄ─╚╦Ż¼ėų┐╔ęįšf╩ŪūįīW(xu©”)│╔▓─ĪŻ×ķ╬─╦╝ŽļĮŌĘ┼Ż¼╠ņ├³ų«─ĻŪ░║¾ø_ä┼║▄┤¾Ż¼ŪĘ╚▒ę╗³c╩Ū╔ŅČ╚ķ_Š“▓╗ē“ĪŻ╦¹Įė▀Bīæ┴╦ÄūéĆ┤¾▓┐Ņ^ū„ŲĘŻ¼▀@ą®Č╝×ķ┴ųų▌╬─ē»į÷┴╦╔½▓╩ĪŻ
ĪĪĪĪ
┼cų«ŽÓĘ┤Ą─╩Ū║┬ä”ŲĮŻ¼╦¹ļm╚╗ę▓īŻĖŃ▀^Äū─Ļ╬─īW(xu©”)äō(chu©żng)ū„ĘĮ├µĄ─╩┬Ż¼Ą½╦¹╦╝┐╝ČÓīæĄ─╔┘Ż¼Ž¦╣P─½Īóž¤(z©”)╚╬ąįÅŖĪó▓╗ĄĮūį╝║ØMęŌĢrĮ^▓╗─├│÷üĒ╩Š╚╦£ÉöĄ(sh©┤)ā║Ż¼╦¹ąĪąĪ─Ļ╝o(j©¼)Ģr▓╗ų¬╦¹──üĒ─Ū░Ńé„Įy(t©»ng)Ą─└Ž╬─╚╦’L(f©źng)╣ŪĪŻą╬ė░ŽÓ╠Ä╩«ČÓ─ĻŻ¼╬ęų╗┤µŽ┬üĒ╦¹▀@╩ūĪČ╝─šZ└§╝ę£ŽĪĘąĪįŖŻ¼╬ę┐┤│÷╩ųĘŪę╗░ŃŻ¼╩Ūėą¬ÜĄĮų«╠Ä╔ŅÕõĄ─┴”ū„ĪŻ╦¹▀Ćīæ▀^ę╗Ų¬╚f░čūųĄ─ĪČ³S═┴Ąž╔ŽØL│÷éĆ╦Į╔·ūėĪĘŻ¼į┌20╩└╝o(j©¼)90─Ļ┤·╩Ū║▄ėąø_Üó┴”║═ßśī”ąįĄ─ĪŻ╬ęę╗ų▒▓╗═³─Ū╬─Ą─ś╦(bi©Īo)Ņ}ĪŻ
ĪĪĪĪ
ŚŅ┼Ó╔Ł╩Ū├”╣½äš(w©┤)Ż¼╚½┴”Å─Į╠ė²╚╦Ż¼¤oŽŠ╬─īW(xu©”)äō(chu©żng)ū„Ż¼╬ęį°ą”ĘQ╦¹╩Ū┴ųų▌Ą─┐ūūėŻ¼╦¹šf╦¹╩ŪéĆŪ┌ļs╣żŻ¼┼c╬─š┬▓╗š┤▀ģŻ¼Ą½╦¹Ą─╬─ūųėų┤_īŹ║▄╣żš¹║▄ęÄ(gu©®)ĘČŻ¼┴”Č╚┤¾ĪŻ╔ŅÕõ├¶õJĄ─ųŪ╗█Ż¼į┌ūų└’ąąķgķWų°▀═▀═▒Ų╚╦Ą─╣Ō├óĪŻŪę┐┤ĪČäóéõ×ķ╩▓├┤▓╗─▄Ą├╠ņŽ┬ĪĘųąĄ─┴óęŌšōō■(j©┤)ęŖĮŌĪŻŲõų¬ūRīė├µĄ─žS║±Ż¼ęįų┴ŠÜŠõĄ─ę╗ūų▓╗╝ė¤o£pĪŻį┘┐┤ĪȵŽČĪĘŻ¼ī”└Ņ╔╠ļ[╩╦═ŠĪó╝ęŠ│ĪóŪķ╚╦Ą─╔Ņ═Ė┴╦ĮŌ┼c▐qĮŌŻ¼ĮzĮz╚ļ┐█Ą─ė╔═Ō╝░ā╚(n©©i)Īóė╔╔Ē╝░ą─Ż¼Ūķ┼c└ĒĪó╝ę╩┬ć°╩┬░▓╬Ż╔├ūāĄ╚Ż¼Š═╬ęéā▀@ę╗ėńąĪąĪĄ─╔ĮÓl(xi©Īng)Č°čįŻ¼ėąÄūéĆÅ─╬─Ą─╚╦Ą─╦╝ŽļŠ│Įń╬─ūų╣”┴”─▄▀_ĄĮ╚ń┤╦═Ļ├└Ą─Ąž▓ĮŻ┐
ĪĪĪĪ
į┌┴ųų▌╬─╦ćĮńŻ¼▀ĆėąÄūéĆėąļpųžė░ĒæĄ─╚╦Ż¼╚ń╬ęĄ─Ól(xi©Īng)³h╔ĻĘ³╔·Ż¼╦¹╝╚ū÷╬─╩┬╣żū„ėųŪ┌Ŗ^╣PĖ¹Ż¼ė╚Ž▓įŖū„Ż¼Ą½╦¹ī”┴ųų▌╬─╦ćĮń▀Ćėąę╗┤¾ĘŅ½IŻ¼▒Ń╩Ūį┌╦¹Ą─ĘeśO┼¼┴”▓▀äØŽ┬Ż¼│╔┴ó┴╦ÄūéĆģf(xi©”)Ģ■Ż©Ųõųąėąū„╝ęģf(xi©”)Ģ■ĪóįŖį~īW(xu©”)Ģ■Ż®Ż¼▀@ī”┴ųų▌Ą─╬─╦ć╩┬śI(y©©)īó«a(ch©Żn)╔·╔Ņ▀hĄ─ė░ĒæĪŻ
ĪĪĪĪ
į┘ę╗éĆ╚╦╩Ū╣∙├„╔·Ż¼╦¹Ą─╬─╣P║▄ėą╣”Ę“Ż¼ū„ŲĘ║▄ėąņ`ąįŻ¼ńŖÉ█╬─īW(xu©”)ęÓįńĪŻ║¾ļm╣½äš(w©┤)Ę▒├”Ż¼╚įŪ┌ė┌╣PĖ¹Ż¼│Żėą╬─š┬├µ╩└ĪŻĄ½╦¹Ą─Ė³ČÓĄ─ārųĄ▀Ć╩Ūį┌×ķ▒Ŗū„╝▐ę┬ĪŻ╦¹ų„╣▄Ą─ĪČ┴ųų▌ĪĘŻ¼╝╚Ģr┐╠▓╗═³╬─Įńą┬┼¾└ŽėčŻ¼ėųĮo╦¹éāę╗Ų¼╠ņĄžŻ¼š╣╩Š▓┼╚AŻ╗╝╚▓╗öÓ░l(f©Ī)š╣ą┬╚╦Ż¼ėų£Ž═©╦─ĘĮŻ¼įćŽļ╚ń╣¹ø]ėąĪČ┴ųų▌ĪĘŻ¼┴ųų▌╬─╚╦īó╩ŪČÓ├┤¤o─╬Ż┐
ĻÉ║Ż╔·ĪóŪžų▄ĒśĪóÅł▀\╔ĮĪóė┌▒¬╔·Ą╚ę▓Č╝╩Ūį┌Ę▒├”╣½äš(w©┤)ųąŻ¼ęŖ┐p▓Õßś╣PĖ¹Ą─Ż¼╦¹éāĄ─ū„ŲĘŻ¼×ķ┴ųų▌╬─įĘį÷╠Ēų°ę╗ĘN╔·ÖCĪŻęč▓╗āHāH╩Ūę╗éĆ╚╦īæīæČ°ęč┴╦ĪŻ
ĪĪĪĪ
┌wĘ▓ų«╣”Ż¼į┌ė┌╦¹░č╚½╩ąą┬└ŽįŖį~ū„š▀önį┌┴╦ę╗ŲŻ¼ė╔┴ŃąŪĄ─╔ó▒°ė╬ė┬Ż¼ą╬│╔┴╦ę╗ų¦įŖį~äō(chu©żng)ū„ĻĀ╬ķŻ¼ę╗░ŃĄ─┐┤Ę©Ż¼įŖį~╩ŪéĆ└õķTŻ¼Ųõū„š▀╔┘ą└┘pš▀ęÓ╔┘Ż¼Įø(j©®ng)┌wĘ▓ĮM║ŽŻ¼ģs│╔┴╦ÜŌ║“Ż¼Ūęäō(chu©żng)ū„│╔╣¹└█└█ĪŻ┌wĘ▓Š²╚╗║╬ę¬╚ń┤╦¤o╦ĮĘŅ½IŻ¼Ė╩║─Ųõ┴”Ż┐į┤ūį╦¹ŪÓ╔┘ų«Ģr▒Ńī”įŖį~Ą─ńŖÉ█Ż¼╣╩═╦ą▌║¾Ż¼▓╗ŅÖ─Ļ└Ž¾w╚§Ż¼āAą─Ę■äš(w©┤)╬─ėčŻ¼▀@ĘNŠ½╔±īŹ×ķ┐╔┘FĪŻ
ĪĪĪĪ
╬─╝»ųą╩š┴╦Äū╩«╩ūįŖū„Ż¼Č╝╩Ūėą╣”┴”╣”ĄūĄ─Ż¼║├ū„ŲĘūųūųŠõŠõį┌ķWĀqų°╣Ō├óŻ¼ÅV┤¾ūxš▀┼c╬─┼¾ūįĢ■ėąĖ▀šōĪŻ
ĪĪĪĪ
╦∙╝»ū„ŲĘŻ¼’@╚╗╩Ūļs┴╦ę╗ą®Ż¼Ą½ę“ųTę“ėų¤o┐╔─╬║╬ĪŻ
ĪĪĪĪ
ą“ĘŪą“Ż¼¢|└Ł╬„│Č┴╦▀@├┤ČÓŻ¼ üyČ°ļsĄ─įu³cų╗╩ŪéĆ╚╦ų«£\ęŖŻ¼ļy├Ō▓Ņ╩¦Ż¼═¹ėąūRų«Š²ĶbšÅĖ▀š²ĪŻ
ĪĪĪĪ
ĪĪĪĪĪĪ
ĪĪĪĪ
ĪĪĪĪ
ĪĪĪĪ
ĪĪĪĪĪĪ
2007.8.10 ė┌┴ųų▌║«╔ß
ĪĪĪĪ
ĪĪĪĪ
ĪĪĪĪ
Ż©┤▐Å═(f©┤)╔·Ż¼░▓Ļ¢╩ąū„╝ęģf(xi©”)Ģ■ų„Ž»Ż¼┴ųų▌╩ąū„╝ęģf(xi©”)Ģ■ų„Ž»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