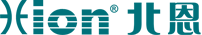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歷程比作一條線的話,那么,線的“頭兒”,就拴在“畢業分配”上,而線的“尾兒”則系在“悲壯獻身”上。
這條線上所串的“珠子”,便是楊凡在暫短的教育生涯中看似“不起眼”實質是“了不起”的許許多多“教書育人”的小事,將這些“小事的平凡”串成“精神的偉大”,使這線上所有的“珠子”無不閃耀著“主人公”追求生命價值的熠熠光澤,而這種光澤能自然而然地與小說中塑造的韓雪、劉翠蓮、趙衛東、鄭潔、曾顯慶、楊春霞、余英等一系列人物的亮點抑或黯淡形成相互輝映和彼此反襯,足見作者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藝術造詣和審美意趣上積羽沉舟、集腋成裘的創作本事。“這條線”最終惜墨如金地以“追悼會”戛然打結,確實恰到好處地體現作者彰顯和歌頌“師魂”的初衷。
偉人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個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作者的“初衷”當屬于這種“正確的思想”的范疇。那么這種“初衷”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當然不是,倘若究其所滋生的土壤,不得不說它與作者教育生涯緊密相關。
筆者從本書作者當年的得意門生,如今已奮斗成名的青年作家王大學撰寫的《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讀馮宗敬老師 <師魂>想到的……》一文中得知,馮宗敬從事教育事業四十多年,現已退休,“在德昌縣教育界可謂德高望重,桃李滿山”。我們從本書作者《后記》中,也不難看出馮宗敬著書立說“初衷”的由來。
作者之所以《師魂》為題,創作出這部頗有分量的長篇小說,其目的是“用以激勵人民教師”,“將此精神發揚光大”。教育崗位的同事們,因此,筆者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據說,馮宗敬先生創作這部小說具備得天獨厚的生活積累,他以時代責任感為弘揚“師魂”,最大限度地提純了部小說主題的含金量。筆者愿以一個老編輯的良知負責任地說,這部小說反映的是人民教師的心聲,是踐行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的形象教材,是廣大人民教師用來鞭策自己的一面鏡子。
編《師魂》這部長篇小說,我看見點燃生命的燭光是多么燦爛!筆者感動之余賦詩一首,不知能否與讀者共鳴。
君以忠誠寫忠誠,
書內書外相呼應,
點燃燭光頌生命,
教育生涯見真情。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