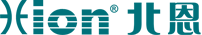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這種“守望”不是靜止的,不是被動的。當我們打開這部詩集的時候,詩人楊進漢在追求繆斯的漫漫路上踽踽而行的身影,會占據你的視野牽動你的視線。筆者擇取“穿行”、“滑行”、“獨行”的三個側面,去折射和透視詩人詩化了的“鄉土情結”之脈絡。
脈絡A:詩歌的小舟在詩人藝術的境界——“美”的漣漪間穿行
如果將詩人的藝術境界比作長河,“美”便是這長河中的漣漪。詩歌的小舟穿行其間,只有善于駕馭者,才能創造并分享這“漣漪之美”。
楊進漢駕馭詩歌的小舟,追日出日落,趕月缺月圓,年復一年,藝術無止境的“漣漪之美”,給了他勇于創造,樂于進取的靈智。
楊進漢的“鄉土情結”被“詩化”后,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已擺脫了非詩人“鄉土意識”層面上的局限性而升華到“詩化美學”的境地。縱觀這部詩集,其詩美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自然之美”,一種是“人性之美”。
“自然之美”與生態密切相關。有位學者撰文說,“生態,我們可以直解為某一自然物所表現出的生命的形態或樣態。作為生命形態或樣態存在的自然,雖然它的形象依然沒有得到充分凸顯和強調,但它畢竟是可以訴諸人的感性觀照的……”對此,筆者即有同感又存分歧。同感是,既然生態“可以訴諸人的感性觀照”,作為占“感性”比重較大的詩來說,將“生態”納入其中,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分歧是,楊進漢的詩以“感性關照”,攝取“生態”的鏡頭綻放著美不勝收的魅力,這怎能說“它的形象依然沒有得到充分凸顯和強調”呢?詩對“生態”具有“凸顯”的特性,《黃昏:難以悟透的景致》、《晚景》就是有力的佐證。“回巢的鷹抬高翅上的眉月”、“霞光打掃著他們的憔悴”、“樹梢 ,若隱若現的手指,拉開夜的帷幕”等詩句,借“鷹翅”和“眉月”、“霞光”與“憔悴”、“樹梢的手指”與“夜幕”的相互關聯照應,“凸顯”出“生態”或“自然”通過詩化后的“美”。從中可見,詩人楊進漢對美學的把握和運用,在詩歌創作上得到主觀和客觀有機結合的能動發揮。
楊進漢的詩,如果說,對于“自然之美”的描繪,具有凸顯的特性,那么對于“人性之美”的反映則具有折射的格調了。《收割秋天》當是折射“人性之美”諸詩中首推的范例。當“我坐在田頭/舔著鐮刀割破的手指”,“面對日漸蒼老的父母”正在“頂著火辣辣的太陽/收割秋天”之時,給他最大的“感受”是“收獲的沉甸”——這種“收獲”便是“父母感激的眼神/開啟我樸素的廉恥”。這里的“廉恥”包含著“我”對“父母”深懷的內疚和感恩,這用“人性之美”點燃的亮點,是通過“火辣辣的太陽”和“盛滿泉水的竹筒”這相對應的意象折射開來的。至此,作者感到“無力吟哦”的“詩句”卻顯得那么有力,有力得能瞬間疏通兩代人隔阻的代溝。《一枚葉子無聲墜落》、《最后的陽光》、《冬天將臨》等詩都不同程度地閃耀著“人性之美”的光環,“我感覺到/一道祖先的眼神”、“您奔赴天堂的路上/炊煙生動,青草久長”、“將姓為炭 ,以名作薪/一筆一畫投入火爐”等詩句,交織著陰陽相隔的血緣牽掛之情。
脈絡B:詩心的熨斗在詩人靈魂的布衣——“土”的風景上滑行
“詩心”,是在詞典里查不到的非現成詞,詮釋它免不了見仁見智。竊以為,能涌出詩之漣漪、詩之波瀾的心謂之“詩心”。“熨斗”,是眾所周知用來熨平衣服或布料的一種工具。筆者之所以將“詩心“和“熨斗”作為本體和喻體焊接在標題上,是為了所表述的“鄉土情結”更加接近詩人楊進漢內心的感悟,又是出于對這部詩集賞析的方便,捕捉一點審美的取向。那么,筆者就用這一連串比喻的鏈接,如此這般地去解讀詩人楊進漢的“鄉土情結”吧:“鄉土”,在楊進漢眼中,是詩人靈魂的布衣,布衣的本身,最容易起褶,因此,“熨”的需要,刻不容緩。且看,楊進漢“詩心的熨斗”是怎樣在詩人靈魂的布衣——“土”的風景上滑行的——
“鄉土”出現人為的“缺陷”,就是詩人靈魂的布衣上的“褶”。作者將這“褶”視為與“土”的風景之“美”不相稱的“丑”,并勇于亮了出來。且看楊進漢筆下的《毛栗灣》:“一代又一代灣里人的饑腸”靠“上了釉的栗子填飽”,可“毛栗樹把果實喂養了灣里人”,到頭來“卻得不到灣里人應有的回敬”,這灣里人竟聽信“風水先生說”的“毛栗樹的青春太旺,霸占灣里的地氣太多,灣里人的陽壽就不長”的迷信之言,在“雜交水稻出世以后”,“腸肥腰圓的灣里人”有了米吃,就忘了本,開始濫伐“有恩于他們的毛栗樹”。這首詩涉及的是環保的大題材,由于濫砍濫伐,在這片詩人視為“靈魂的布衣”的鄉土上就出現了遮不住的“丑”,這丑的“褶”出現了,作者禁得住動了“詩心的熨斗”,要熨平這“丑”的“褶”,于是發出惋惜地詰問:“秋又涼,月再圓,團圓的灣里人喲,是否還有毛栗樹的影子,沉在你邀月的杯底”?這具有打動人心潛移默化的力量,見證了“詩心的熨斗”除“褶”的憂患精神——這種“褶”不僅僅浮現在“鄉土”上,更不可否認的是生在“毛栗灣人”的思想里。在這里,“毛栗灣人”已成為時下“不重視環保者”的同義語。
如果說《毛栗灣》的“伐樹現象”牽動了作者將這“悲劇”撕碎的“美好”讓人們看的話,那么,《親近黃桑》便是作者懷著醫治這“悲劇”創傷的祈禱,發出帶有警示意味的倡議:“親近黃桑,我祈愿/ 斧鋸不再伐傷靈魂/槍彈不再獵取噩夢/美麗不再沾有血腥”。進而,作者的“詩心”終于尋覓到熨平“毛栗灣人”思想里的“褶”后煥然一新的畫面,這一畫面集中在《鐵杉》一詩里得以盡興地展現:“一群樹躲過一場劫難/逃到蒔竹水的源頭//一群樹彰顯起/黃桑自然保護區的靈魂/涵養著苗家侗寨/靈動的詩情//一群樹/ 青蔥著焦灼的心靈/粘合起易碎的人性” 。在這里,通過“黃桑自然保護區”生長著的“躲過一場劫難”的樹們蔥蘢的景觀,彰顯了大自然的偉大和神奇,寬容和公義——盡管人性惡劣畢露,時時對大自然進行著“好吃不留籽兒”式的掠奪,可大自然還是傾其所有,盡其所能,善待我們不配善待的人類——這首詩“粘合起易碎的人性”的箴言,難道不足以引起我們地球人慚愧和反思嗎?造物主創造了我們人類,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甚至是罪犯,都同樣平等公義地供給任何人不可或缺的陽光、水和空氣,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對生我們養我們的地球進行摧殘呢?!在這部詩集里,作者面對“環保惡化”的現狀發出的呼吁,其旨意,與上世紀80年代詩人熊召政詩作的標題“制止,請舉起你森林般的手”同樣發人深省!
本序《脈絡B》標題下所涉及的“褶”這個意向,可理解為“社會問題”的詩化形象。這種形象又在《不合時宜的風景》這輯中得以集中表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官場經濟學》,“打電話”、“寫便條”就能“呼風換雨”,到頭來“終生的財富”卻“濃縮為幾滴眼淚”,“提煉成幾句懺悔”。它的深刻所在,就是用辯證法詮釋了“官場經濟學”,鞭撻寓于其中。
歷代民謠,與民心相通,當今民謠也概莫能外。《民謠》表達了“哭的是愛恨,喊的也是愛恨”的民眾同感共鳴,這首詩以弦外之音道出了“愛恨”產生的根源就在于人世間不會滅絕的“美丑”。《恐懼》的幽默,《白霜》的辛辣,《禪意》的嘲諷,《又見烏鴉》的祈盼等篇什表達所涵蓋的思想意義的過程,就是“詩心的熨斗”去熨“褶”的過程。作者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碰撞的同時,詩人的時代責任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這亦是作者“鄉土情結”經過詩化的提煉的另一種翻版。
脈絡C:詩藝的筆端在詩人求索的旅途——“苦”的寂寞里獨行
鐘愛詩歌需要旺盛的激情,獲得詩藝需要不衰的才氣。詩人求索的旅途,充滿荊棘,沒有甘于在“苦”的寂寞里獨行的勇氣,就會將激情和才氣消磨殆盡。楊進漢在漫漫詩路上求索的足跡,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當年,我在老家黑龍江主持一家報紙副刊和主編《跨世紀新詩人詩叢》,都編發過他的詩作;直至我獨闖北京創辦文化實體運營以來,他依然和我保持聯絡。在創作上,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睿智、勤勉、執著、奮進;在人品上,他的謙和、穩重、誠摯、善良,令我倍加欽佩。筆者一向固執地認同“文如其人”的老生常談,楊進漢就是這樣的人,必寫這樣的詩。他在做人上不會投機取巧,在作詩上不會依賴捷徑。不“投機”卻有“頭機”可獲——謀職落到財政局,寫詩入了省作協;無“捷徑”倒有“結晶”可得——多次獲獎摘桂冠,一部詩集唱心聲。這,不正是詩人楊進漢,用“苦”的寂寞在詩路上鑄就的“求索”的里程碑嗎?
寫詩之“苦”是常人體會不到的。捕捉靈感的輾轉反側,不被理解的冷嘲熱諷,貪黑熬夜的辛勤勞作,學海拾貝的探測尋覓……如此孤獨寂寞,久而久之,對于楊進漢形成詩化了的“鄉土情結”底蘊,起到不可替代的鋪墊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評價楊進漢,一言而蔽之:他是一個地道的獨行者!之所以說他“獨行”,是因為他具有:我行我素的詩人特質,獨辟蹊徑的追求目標,鍥而不舍的堅忍毅力,不畏人言的心理素質。
“序”好比報幕,在《守望鄉土》即將拉開序幕之際,讓我以古風一首權作與本家進漢弟共勉的“開場白”——
愛詩如命苦獨行,
吞月吐日追大風,
我借北斗舀天水,
澆灌心花開幾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