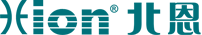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調枯燥卻不失豐富,荒涼空曠卻不失神圣的昆侖山深處,直到2004年5月才被調到昆侖山下某部軍務股工作。也許在他“命運的辭典”中無緣翻到“提干”這誘人的字眼,但他無怨無悔,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履行著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他多次被評為“優秀士兵”,3次榮立三等功。這種“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具體體現在“熱愛昆侖山,熱愛戰士的崗位”的感情和以“祖國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得失”的思想,綜合起來的矢志不渝的心理狀態,不正是一個軍人應有的“情操”嗎?
“作家的氣質”,尤其是軍旅作家所形成的氣質,應以“時代責任感”為第一要素。羅國勤是一位富有“時代責任感”的青年軍旅作家,他以反映軍營生活,塑造當今和平年代中的軍人形象的定向創作選材,加重了“筆”的砝碼。如果有那么一種能衡量作家之心的天平,我想,一定會稱出他那“忠誠”的分量,若用 “金子般的心”來詮釋他的忠誠也毫不為過!這在本書開卷之作《昆侖戀情》中可以找到佐證——這篇小說敘述了一位軍人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小說主人公是出身于甘肅隴南山區七古崖小村莊的山娃子,叫陳東明。他身為軍人,為了履行守衛祖國邊境昆侖山的神圣職責,不能在患骨癌的父親身邊盡孝,不能回家與妻子團聚,只能在妻子來軍營探親時暫短聚首,在地震中失去了幼子盼盼,最終在執行巡邏任務時不幸被雪崩奪去了年輕的生命。當讀者翻開這篇小說時,我相信,一定會被作者筆下在和平年代中那種悲壯且崇高、殘酷而莊嚴的軍隊現實生活題材的典型人物為國捐軀、為信念獻身的動人故事而蕩氣回腸,潸然淚下!于是,軍旅作家的“時代責任感”就這樣在羅國勤的筆下,綻放出“以先進文化教育人”的精神之花。當這種花香彌漫讀者特別是軍隊官兵讀者的心田之際,能不煥發出“真善美”的情愫嗎?能不激發對“高尚”的崇敬和效仿嗎?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不就是作家“時代責任感”輻射力結晶之所在嗎?國勤君,無論部隊組織對你努力做一個“軍營代言人”的自覺行動是否通過一種形式予以嘉獎,你都應感到驕傲,感到自豪,因為你已將自己的“那滴水”最大限度地為時代折射了“太陽的光輝”……不必多言,你的首長和戰友們向你投來贊許的目光,就是無價的勛章。
當軍人,羅國勤的信念沒有動搖過;
當作家,羅國勤的追求始終堅持著。
“有志者,事竟成”,這樸素的哲理,在了羅國勤身上,得到了最有說服力的體現。如今,《昆侖情結》這部小說集出版問世已是水到渠成的事。當“命運之神”青睞地為羅國勤悄悄地戴上“青年軍旅作家”的桂冠時,他深知這頂桂冠是他在業余創作的長途跋涉所斬下的一路荊棘所編——
那上邊串著他那么多“心”的血珠兒,是通過昆侖山凜冽的風刺破他十指而掛上去的;
那上邊串著他那么多“苦”的淚珠兒,是通過昆侖山冰冷的雪寒徹他雙眸而凝上去的;
那上邊串著他那么多“勤”的汗珠兒,是通過昆侖山偌大重負壓痛他兩肩而濺上去的。
于是,羅國勤懂得了“生命的含義”、“軍人的含義”、“使命的含義”,正是為了這三個“含義”,羅國勤的創作追求才“義無返顧”,而這“義無返顧”恰恰是綰成“昆侖情結”的情之所系。
有人往往在唾手可得卻不能得或自認為應得而未得之時,牢騷“命運”之不公,殊不知在眾“神”之中,“命運之神”是最公允的“神”了。古有“塞翁失馬”的典故,便是“命運之神”公允的見證。以拙之見,不妨將羅國勤所付出的抑或所失去的姑且都視為那丟失的“馬”,倘在日后真的會領回個“良駒”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是的,命運方程的“解”并非惟一,它有好多殊途同歸的“解”在等待著志存高遠者去揭曉。筆者作為曾與命運抗爭過并時時敢于與命運繼續較量的人,可以坦率地說,“命運之神”的強大,是強大在你脆弱之日;“命運之神”的脆弱,是脆弱在你強大之時。只要將自己的“命運”牢牢攥在自己的手心,“命運之神”的“死去活來”就掌握在你自己的股掌之中了。
其實,羅國勤是幸運的——
幸運就幸運在,他所在的部隊首長和戰友們,對他的創作乃至出書的關心、鼓勵、支持、幫助,怪不得他能在各報刊雜志、電視臺、廣播電臺發表新聞稿件和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500多篇(首)呢;
幸運就幸運在,他遇上了作家劉龍平、蔣凱等老師,為他不時地指點迷津,怪不得他從詩歌創作很快就切入了小說創作,且抓住自己最熟悉的軍營生活這一大題材不放,以至于運作這部小說集的出版而旗開得勝呢!
作為本書的編者,應作者再三誠邀,抽暇作序,對于羅國勤筆下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特別是作者精神境界的脈絡有了進一步的梳理,感悟頗深。至此序尾,意猶未盡,順作小詩一首,愿與作者和讀者諸君共勉:命運之手亂翻時,驗雨測云憑自知,真才方得回天力,抓住機遇任飛馳!前程漫漫,年輕的軍旅作家羅國勤,你惟有“上下求索”,才能與命運爭個高低上下。愿你以“槍+筆”的熔鑄,造就事業壯麗的輝煌!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