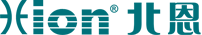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我筆下的“這片月亮”,不是天上的真月亮,她是這部詩文集封面情境的寫意。再確切些說,這片畫在紙上的月亮是從作者的心湖里升起的,是作者人格的練達、個性的彰顯、才智的靈性、理想的執著而綜合冶煉出來的具有象征色彩的一種“圖騰”,是作者獨有的“這片”,而不是“那片”。
事物有自身發展的規律,人有自我成長的軌跡,而“這片月亮”,則有她從缺到圓徐徐升起過程。
直觀地看,“這片月亮”也同“真月亮”一樣,先是淡淡的弧鉤,再是清清的半瓣兒,然后才是朗朗的整圓兒——這何嘗不是張素粉《羞澀的月亮》從創作到問世所經歷的全過程呢。
讓我們從直觀,切入“這片月亮”的內涵。“這片月亮”正是一個完整的括號裹著一個“核”,我們不妨把這個“核”,視為《羞澀的月亮》題旨的核心。
那么,其“題旨”的核心是什么呢?當我們讀過上卷的103首詩,下卷的27章隨感后,會給我們留下一個較為完整的印象。那就是:作者以自已的藝術視角,大多截取與“美”糾葛交織在一起的現實生活零碎“鏡頭”打造成詩。當然,這種“美”是經作者情感天平定位后,升華或篩濾過的——
“戀”的“氤氳之美”。“氤氳”一詞原指云氣濃郁。移植這里,狀喻涉及到“戀”的詩文所特有的被“云氣”般的氛圍所濡染的一種美。如《你是誰?》:“我日日思慕的你,哦,你是誰?/
在蒙著灰塵的喧鬧街市嗎?不,你不在這里/
這里所有的面容都帶著匆匆的灰色憂郁//……我日日思慕的你,哦,你是誰?/
在柔情蜜意的歡聲笑語里嗎?不,你不在這里/
這里包容的感情都懷著目的和野心//我日日思慕的你,哦,你是誰?/
竟讓我心甘情愿走在長長的相思里/
時刻感受著,那在徐徐清風中行走著的……//
——哦,你是誰?”詩中思慕的戀情欲言又止,若隱若現,被一種未知的疑惑裹著,使“你是誰”的“?”,在“氤氳”之美中飄浮不定,與“猶抱琵琶半遮面”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妙”在不少篇什里都有所體現,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喻”的“脫俗之美”。在《 嵩山對泰山的夜語》一詩中,作者把“嵩山”和“泰山”喻作天各一方相愛的人,這對相愛的人只能讓彼此“各漂一方的魂魄,緊緊相偎在夢里”,而將“各自成就一番天地”視為“是彼此間最高貴的獻禮”,至此,他們的愛升華了。這種升華,在“回頭愁情萬種的相視”遙遠而咫尺的距離間,體現得淋漓盡致,給讀者的視野拉出一條無形的線,將“嵩山”和“泰山”連在一起。他們是相背而立,或相背而行,不然怎么會彼此“回頭”呢?然而,他們為什么相背,這在“攜手撒珠璣給山林”這句中找到了答案,他們為了這樸素的事業,竟“沒有窩巢供我們安然享樂”,這種追求無疑是高尚的。作者將生活的某些體驗藝術化,在“本體”和“喻體”選擇的和諧上煞費苦心,營造出“喻”的“脫俗之美”。
“痛”的“凄迷之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只不過“痛”的緣由各有不同。作者在這部詩文集中所表達的痛,大多是由美好的事物或美好的情感所引起的。“可愛的言語/可愛的眼淚/別再彼此折磨//待來生或許滿園都是/你想要的各色各樣的果(《此時的心情》)。”這種忍痛的勸慰,是由“深情隨花飄落”而引起的。這“花”或指一段愛的經歷,或指一件事的追述,或……總之是一種“飄落”的“花”。作者在這里將“花”演變成“各色各樣的果”的期待,然而,花落已成定局,其“痛”的“凄迷之美”便飄然而至了。 “盼”之“澄澈之美”。作者筆下《隨感二十七章》中的一些篇什,渲染了“盼”這一常人期望的美好情感。《職業和事業》,期望“職業和事業”和諧的“盼”;《停電——來電》,期望孤寂時有愛人陪伴的“盼”;《磁力》,是思念萌動后期望“燃燒濃烈的火紅”的“盼”;《如同尋夢的孩子》是期望“你”打開“塵封”的箱子“把往昔講給我聽”的“盼”……“盼”之種種,讓讀者如臨作者的心井之前,一眼見底,這“澄澈之美”,便是毫無做作自然而然的美了。
作為本書系主編,有責任從扶持文學新人的角度提示給作者:我之所以未把“這片月亮”寫成“這輪月亮”,下筆是極有分寸的。“片”與“輪”這兩個量詞,則有前者單薄后者渾厚之分。天上的月亮圓了會缺,這大自然的規律同樣可以與你這片“詩文的月亮”類比,你用你的筆在自己的文學天地里劃了一個圓兒,這圓兒是階段性的句號,當你時過境遷后再回眸審視,那些缺點就會烘云托月般地洇出來,至于你是否能覺察到,要看你自己的領悟了……
“領悟”很重要,它是根植人心田的菩提樹,德行、才智、善良、純真、正真、坦誠、自醒……都是澆灌它不可或缺的養料。愿作者心中的菩提之樹蓬蓬勃勃蔥蔥蘢蘢!
應本書作者盛情難卻之邀,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