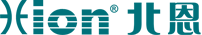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一、作者的“苦難經歷”已成為創作的“突破性泉眼”。
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作者正值風華正茂的求學時代,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過豐順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的父親竟含冤入監獄,從此,作者便刻骨銘心地體驗著苦難的冷酷。如果說父親入獄是下了一場“雪”的話,那么,“文革”無疑是加了一層“霜”——這“雪”是狂的,這“霜”是厚的,致使作者苦難的“冷酷”達到“無情”的程度,那心靈上漫長的“結凍期”將作者人生的境遇冷降到冰封的“低谷”。
在這冰封的“低谷”下,作者找到了創作汲取生活的“泉眼”,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時作者賴以生存的環境除了這“泉眼”有些涌動的活力之外,其他便似乎全是凍結的壓力了。這“壓力”與“活力”,形成了“兩種力”的對峙,事實上,作者在無力改變的“大氣候”的特定環境中,這“活力”對緩解“壓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作者有詞為證:
彈淚長吁,矯首處,珠海云月。吹悶簫,聲嘶音啞,心頭如噎。不堪回首情和夢,難顧當前名與節。跑長街,揀破紙爛鐵,羞惻惻!
遺憾事,休提說;擊長鋏,生計絕。嘆衣衫襤褸,糧金盡竭。讀書無心因饑腸,踏破鐵鞋謀職業。銷魂也,滔滔南流水,何時歇?
這是作者時值1962年6月20日,陷于“被學校辭退,好長時間找不到新的工作,收入全無”的窘境之中,所作的一首詞,自稱“游戲之筆”。悲哉!壯哉 !好一個“筆”下之“游戲”——自尊,隱于“羞惻惻”;自強,寄于“跑長街”;自憐,囿于“名與節”;自嘆,問于“何時歇”。君正是:職業雖丟志沒丟,生計欲絕筆未絕,面臨沉淪未沉淪,難顧名節重名節。因此筆者說,作者的“苦難經歷”已成為創作的“突破性泉眼”,相信讀者會有同感。
創作的“泉眼”,一旦“突破”,便呈淙淙流淌之勢,于是乎,詩詞之潭,散文之溪,小說之河,“三流”之聚,集中體現了作者“立足現實,忠實現實,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再現現實,反映現實”(引自作者《創作漫談》)的創作傾向。這種創作傾向,導致作者“懷舊情結”的生成,作者憑自己良知的“攝像頭”拍下了“苦難經歷”的若干鏡頭,我們通過現在的眼光過濾那些紛紜復雜的歷史,依稀可見創傷過后的“痂”。作者不是用粉飾的“激光”去修那“痂”,而是用犀利的筆鋒戳開讓世人看,使同時代的經歷者回顧痛楚而溫故知新,令未曾涉過此境的后來人閱覽前車之鑒而未雨綢繆。如果用本書的作品為鏡,去鑒別現實中“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語)與“繞過歷史彎子”的兩類作家,無疑,思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這也是本書作者創作“突破”之所在。事實證明,大凡有“苦難經歷”者,更有“責任感”,這是時代賦予的。思云先生就是有時代責任感的作家,讀者不論讀過本書的任何一篇作品,都會有此體味的。
二、本書的“原汁原味”已成為作者的“意趣性審美”。
筆者就此淺談拙見,但愿權作為讀者品嘗思云釀就作品的陳年之酒而開塵封之蓋的舉手之勞。
所謂“意趣性審美”,即指作者以自己置身于人生體驗而積淀的意趣去潛移默化地制約審美取向。鑒于此,保持“原汁原味”的作者初衷,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僅就《思云中短篇小說卷》的作品而言,筆者理解作者的“原汁原味”的“原”,應為取材于特定歷史背景的真實,而“汁”和“味”則該是在這個特定歷史背景下,作者撒進自己獨有的“審美要素”調和而成。這種“調和”,就是通過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對事件過程的取舍,對情節脈絡的梳理等創作加工,終極目的是為了抵達藝術的真實。通俗一點講,就是“歷史背景”必須還原,故事情節可以編造。因此,應該說,作者主張的“原汁原味”是尊重歷史的前提下,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創作規律的。
筆者翻閱本書的中短篇小說作品,不難看出作者“歷史背景不變,故事情節各異”的創作路子。五篇作品少則以一萬來字,多則以一萬四五千字的篇幅,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反映“文革”前后發生在廣州城鄉“知識青年”生活中情戀的故事。五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我”——除《來自早春的戀愛》中的“我”是“石老師”、《愛的呼喚》中的“我”是“靜文兄”之外,《我們都還年輕》、《這里的山花不再爛漫》、《抽刀斷水水更流》中的“我”均未透露姓甚名誰。可能有的讀者讀后或許會說,這個“我”就是作者本人,筆者認為這種想法是狹隘的;那么,倘若我們反之輕易得出這個“我”就與作者毫不相干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也未免太絕對了些;如果說這個“我”或多或少帶有作者的影子,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恰到好處的。那么,以上關于“我”究竟有多少作者本人的成分的三種觀點,肯定有一種接近事實真相,我們大可不必去責怪其他兩種不符事實或有悖事實的觀點。正如有的編輯對作者的“原汁原味”存有某些不太認同之處一樣,作者只管我行我素地“原汁原味”下去就是了。至于對“原汁原味”的褒貶評說,自有讀者公論,它不受制于作者的意圖,更不受制于寫序者的導讀。藝術的本身就是見仁見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嘛,出現“一邊倒”的現象反倒不符合藝術鑒賞規律的。筆者認為,應該首肯的是,作者筆下生的是“花”,至于這“花”香到什么程度,與評論家或讀者的審美嗅覺相關,也與其審美取向相關。這與賞花同理,有人喜歡牡丹,有人喜歡茉莉,我們只能說他們的審美取向不同,絕不能武斷地定論誰是誰非。作者的“原汁原味”也是一種花,這種花是為它的喜愛者而開放的,不喜愛這種花的人,也大可不必掐其蕊、折其莖、斷其根,因為這種花的存在,決不影響你的眼球去另覓你的吸引,給你不喜歡的花,留有他人喜歡的余地,是當下“百花齊放”寬松和諧的環境中,作為編輯、作為讀者不失道義的美德。當然,作者若將你培育的花,一概按自己的理由,置人家喜厭而不顧,一味地塞給人家欣賞,也是一種糊涂的徒勞。作品的面世,作者和編者,首先要想到適合的“受眾群”。“原汁原味”的作品,一定有它的“受眾群”,因此本書的價值取決于出書后實踐的驗證,寫序者的文字,只能是一家之言,無論作者編者對其作品的“價值觀”是否一致,都不影響該作品問世后在讀者中發揮的實際價值。
當“那爿歷史之幕”被你徐徐拉開,思云先生,筆者的“序”該到“謝幕”的時候了。夜深人靜,吾心不靜,余興未盡,吟新體駢賦幾韻,以賀君書問世——
馮公立教壇文壇,如竹有節;思云寫親情愛情,似水流瀉。作詩歌,千頭萬緒善理頭緒,情切切;著小說,一波三折喜掀波折,意貼貼。筆觸無界,意境有別。人離合,月圓缺,事滄桑,緣斷接。梅之骨,寒凝;松之韻,雪疊。君書宛紅花,吾序猶綠葉。日月不滅,友情不絕!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