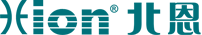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我說鄭洪然會寫詩,是因為他的詩大都以“形象思維”取勝,即使運用了“邏輯思維”,也是在“形象思維”的統領下擇而用之的。打個比方,如果在一首詩的語境形象中,作者先東抓一“鱗”,西抓一“爪”而欲成詩的話,接下來便應擇其與“鱗”、“爪”有關的意象,去南抓一“云”,北抓一“水”,從而塑出“龍”的形象;但有了自地之“水”向天之“云”騰云駕霧、閃鱗舞爪地飛騰起來的“龍”還不夠,尚缺“點睛”,這點睛之筆,便是詩的靈魂之“核”。這種形象的和諧,是抵達詩之佳境的有效途徑。試想,若東抓一“鱗”、西抓一“羽”,南抓一“樹”,北抓一“一花”,這些意象拈在一起就不倫不類了,其“詩象”就似“龍”非“龍”,似“鳥”非“鳥”了——若說是“龍”吧,其“羽”與“龍”無關,其“樹”、其“花”與“龍”也有牽強附會之感;若說是“鳥”吧,“羽”、“樹”、“花”倒與之和諧,可“鱗”就與“鳥”大相徑庭了。這“類別”歸屬,則是“形象思維”統領下的“邏輯思維”。鄭洪然寫詩,深悟其道。能為筆者這一淺論提供例證的詩,在《鄭洪然詩選》中比比皆是。
有證為證之一:《懷念》
懷念,把你懷念成
——一汪湖水
在這多雨的季節
湖水一個勁地猛漲
湖滿了
堤決了
堤內、堤外
處處有你的身影
懷念,是一種心情,是一種心理活動。它看不見,摸不著,生于心,藏于心。怎樣使懷念的感覺化為視覺,只有會寫詩的人才有這種本事。鄭洪然將“你”懷念成“湖水”,而且很有分寸地用“一汪”限定,開始是“一汪”,繼而將“詩象”的境地置于“多雨的季節”,那“湖水”不猛漲才怪。漲著、漲著,“湖滿了”,“堤決了”。到此,懷念的形象比擬已完成,懷念的激情已推向沸點,可作者仍未滿足,便出語不凡順理成章地牽出“堤內、堤外 / 處處有你的身影”的點睛之筆。這首詩“湖水”、“多雨的季節”、“猛漲”、“湖滿”、“堤決”是形象思維的鏈節,它是按照“邏輯思維”的“同類歸屬”鑄就的。在這首“詩象”中沒有多余,甚至沒有雜質。作者將所感表達成所見的澄明之美,沒有一定的審美功夫,是達不到這等境界的!
有詩為證之二:《無淚的離別》
那次無淚的離別
不過是沒有色彩的氣球
放飛它吧
讓它爆破在迷茫的太空
落下碎碎的記憶
就像深秋的焦葉
唉!一片、一片、一片
撒落我荒涼的心田
歲月如風
剛把一片片殘葉吹走
緊跟著
又撒落一片、又撒落一片……
在作者的筆下,“離別”比作“氣球”,離別“無淚”,“氣球”也“沒有色彩”。這種“無淚的離別”如同放飛“沒有彩色的氣球”,離別后,就如“爆破在迷茫天空”的碎屑。繼而,又將這“碎屑”比喻成“破碎的記憶”,轉而,又將這“記憶”用“焦葉”替比,撒落“心田”,襯出“荒涼”。這種“離別”留下的“片片殘葉”被“如風”的“歲月”剛剛“吹走”,“緊跟著 / 又撒落一片,又撒落一片……”傷感的“后遺證”化作“精靈”作起“妖”來,攪得讀者身臨其境,不得安寧。
舉一反三,我已舉二,無再舉之必要。像“我 / 一想起她 / 她——/開放”(《一枚記憶的花朵》);把“日子”比作“幾顆鋼板 / 在口袋里 / 我一路走 / 一路丁當響”(《日子丁當響》);“那滾落的露珠 / 一滴一滴都是思鄉情”(《故鄉情》);“你和媽 / 是這個破屋的兩根柱子 / 你一倒下 / 媽媽就撐不住了“(《中秋情懷》)”;“就像雨水淋濕了我的衣衫 / 我這瘦老的身軀 / 似乎也激動得 / 快冒出新芽”(《雪花飄過了》)等等俯拾便是的佳句,其妙不可言之處就留給讀者品味了。
鄭洪然在把握一首詩的整體形象和諧的同時,特別注意“煉字”,這大部分體現在動詞的選用上。如“就像我椅背上的那張死虎皮 / 會在睡夢中撲過來 / 把我嚼醒(《那件事》),這節詩中的“嚼”就像“好鋼用在刀刃上”一樣,“嗖——”割開想像之膚,讓“奇妙之痛”,入骨三分;試想,如把“嚼”替換成“驚”,就會將“入骨三分”蛻化到“不痛不癢”。
本文開頭,筆者將“兩類寫詩的人”分為“會寫詩者”和“不會寫詩硬寫者”。“會寫詩者”以鄭洪然為例,就其詩的寫法,進行了言之有據的梳理和剖析;有對比才有鑒別,筆者愿不揣淺陋,為“不會寫詩硬寫者”,也“有的”放它“一矢”——
刻薄地說“不會寫詩硬寫者”,“連詩是什么滋味,根本未嘗過,別說是詩之“精髓”,就連詩之“皮毛”都未知一二,其成詩的方法往往是東拼西湊,簡單分行,人云亦云,依樣畫瓢;其至緣木求魚,將胡涂亂畫之物硬充其為“瓢”,那“瓢”里裝的必然是“華麗辭藻”抑或根本無“華麗”而言,甚至連“辭藻”都算不上的“雜燴”。如果這種人是剛“觸詩”者,也情有可原,也許因尚未撞擊到“靈感火花”所致;可這“不會寫詩硬寫者”并不全是剛“觸詩”者,有的寫了十年八年,甚至半輩子,一輩子還認不出詩的本來面目,且舊轍重蹈,一味造自已認為是詩的“分行文字”,這就不能不說是可悲已極了!
可以說,《鄭洪然詩選》與“會寫詩者”的詩集為伍毫不遜色,在“不會寫詩硬寫者”面前,堪稱具有“教材意義”的文本也不足為過。
讀過此文,也許有人發問,“會寫詩者”和“詩人”有何區別。筆者答曰:詩人,一定是“會寫詩者”,而“會寫詩者”不一定全是詩人;筆者固執地認為,“詩人”不但會寫詩,還要會做人,詩品人品雙佳才可稱得上“詩人”;而“不會寫詩硬寫的人”,無論人品如何,也稱不上“詩人”;人品若好,不論詩作得如何,都是好人。從上述的意義上講,鄭洪然配得上“詩人”的稱謂,因為他除了會寫詩外,平素做“好人”的本性未變,這在我與他多年交往的緣份中可以求證。邀序寫就,紙短言長情未了,口占一詩,書于序尾,以記詩友之緣。
詩人憑詩立詩壇,
好人得好自平安;
人若如樹詩如果,
品詩品人亦品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