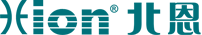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葉;
看似未飛其實早已飛向遙遠的記憶的紙鶴;
在秋的繽紛中隱喻很深卻免不了凋零的白菊層層疊疊地開過又一瓣一瓣地謝過盡情地鮮艷過也忍痛哭泣過的玫瑰……
哦,彩貝、紅豆、淚珠、蝴蝶、紅葉、紙鶴、白菊……它們交織著變形的惆悵、壓扁的寂寞、靜止的流盼、消瘦的相思、凍結的離愁、定格的笑容、塵封的情緣、開花的期冀……構架了《我與水之間》想像空間的藝術氛圍。
夠了,僅從以上意向就不難看出作者對善良、對真誠、對事業、對藝術、對愛情、對人生帶有美好色彩的一切的追求。我說,這就是作者童玲寫《我與山水之間》所蘊涵的“她與山水之間是什么”的內在精神世界。
“蘊涵”,不是直白的流露。散文詩,首先是“詩”,其次是“散”,“詩”是骨肉,“散”是包這“骨肉”的“皮”——我是這樣理解,恐怕童玲也有同感吧。童玲有理解散文詩真諦的天分,她有能力將漢字語言符號與情感暗示渾然一體地折射出對生活的藝術感知,而不是依樣畫瓢地描摹生活。我以為,這便是“詩”與“非詩”、“藝術”與“非藝術”的最基本的界定。可以說童玲自覺不自覺地以自己的悟性逐漸遠離那些“非詩”、“非藝術”的因素。當然,童玲的筆下攝取的生活面還不夠寬泛,所寫作品的藝術質地也并不那么完美無缺,除了個人情感還有更寬的天地可任“散文詩之鳥”振翅高飛,隨著童玲思想和藝術羽毛的逐漸豐滿,別有洞天的境地會等待著她遲早的棲落……
在此,我不想再舉些童玲散文中類似“整整一個秋天,孤獨了的樹木漸漸成為了一根思想的骨架”這樣的妙言佳句賞析,留些余地讓寫詩的和不寫詩的讀者朋友玩味吧。
為了讀者對此書有個比較清晰的閱讀脈絡,作為編輯,在大致揣度出作者的意圖后,將這些結集的散文詩分為三輯,以饗讀者。
作者再三邀請作序的誠摯不好推脫,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