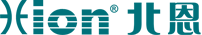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起平坐的含義。這就是我對朋友內涵的領悟,換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常說的那句最樸素的話“以心換心”。從這個角度講,“禮尚往來”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就蘊含其中了。我固執地認為,如朋友有主從之分,上下之別,大小之念,那就不是真正的朋友了——我的個人觀點,仍可在漢字的結構上找到自圓其說的注腳:那就是當“朋”被偷梁換柱成“明”的時候,便成為挑“明”了的“借光”關系。追其根由,是因為“朋”的其中一半——“月”,很不講究地撤掉了友情得以支撐的兩根“柱子”,異化成“日”之后,“朋”失去了平衡。“日”自以為擁有“光”可借給“月”而自大起來,殊不知,由于他們關系性質的改變而疏遠了之間的距離,因此“日”離“月”越遠,就顯得越渺小。當然,朋友間借“光”,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倘將這“光”被換算成“孔方”,且明要硬索,那就玷污了“朋”的本真含義。
我來京后業務仍與編輯有關,少不了與老友們再續筆墨之緣。鄭天送又寄來了他第二部詩集《心泉吟》的打印稿,向我陳述出書的愿望,并執意懇求我再次作序,還表示要付費的。序,我答應作;可費,說啥也不能收。理由很簡單——一我不是名人,所作的序一文不值;二我不是商人,決不做拿“序”換錢這“取之有道”的“君子”。現在“不”,以后也“不”!名人作序收錢無可厚非,因這里面有“名人效應”的含金量;商人受財天經地義,不賺錢投資經商干什么。而我這個“非名人”作序撈錢,豈不連自己也會罵自己“無名手黑”嗎?!我這個“非商人”啥“財”都受,豈不讓別人罵我“不商也奸”嗎?!我這個人做事有個起碼的自律,“自己罵自己”的,不能做;“自己被別人罵的”,更不能做!富也“不”,窮也“不”!
說實話,我本來很忙,可推卻為其作序又恐落個“楊楓這小子到了北京忘了朋友”的話把兒。這話把兒攥在朋友手里了不得,拋過來就會砸我一個跟頭!我這樣嘴無遮攔,是對朋友的坦誠——我向來不相信和朋友“揣心眼兒”的人,會交到真朋友。可以坦率地說,我作這個序,一半是為朋友,一半是為自己。因此,天送兄大可不必感謝我,你多匯的錢,用在出書的刀刃上,書盡量厚一些,紙盡量好一些。
這哪像為朋友作“序”,倒覺得有點為自己作“敘”。不過,文無定法,作序亦然,“序”也好,“敘”也罷,不偏離“友情”,就不算跑題兒。
在與鄭天送的交往中,無論是閱他的詩稿,還是讀他的信,他都迫不及待地表達要做“時代歌者”的渴望。我想,“時代歌者”不一定非“大手筆”莫屬,“小人物”想頂起這一桂冠,更難能可貴!我說,天送兄,您這種渴望是高尚的,近乎不摻雜質。這種渴望的清澈,怎能不令我為之感動!
“時代歌者”,其精神內核不外乎“為時代而歌”。作為年過花甲、體質較弱的鄭天送來說,能義不容辭地肩負“時代歌者”的重任,這種“小馬拉大車”式的超負荷,不知傾注了多少的心血!
鄭天送的“執著”,在世俗的眼光里,會釋義為“傻瓜”。可他不理會這些,頂著冷嘲熱諷,依然鍥而不舍;與疾病抗衡,日日筆耕。他在稿紙的田園里播種,所選的“種子”,無不過他的“思想之篩”,他的詩注重“政治標準”,講究思想性,這是他做“時代歌者”必須遵循的原則。從中可見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忠誠于黨、忠誠于時代的赤子之心。
也許有人讀鄭天送的《心泉吟》,會有一種“不那么藝術”的感覺,這在某種程度上道破他某些詩作的弊病。不過,類似這種詩總在“這一類”作者甚至亦被稱其為“作家”、“詩人”的筆下倔強地怒放。是“花”也好,是“草”也好,起碼它們是無毒無害的,作為編輯不該以自己的好惡輕易扼殺它,給它以生長的園地沒什么不好。
整體看,《心泉吟》大致歸于謠體創作之范疇,也有其自己的特點:曉暢易懂,不晦澀;合轍押韻,不拗口;謳歌時代,不做作;積極向上,不媚俗。鄭天送的詩歌創作走勢與“詩言志”很合拍,也是與其行為規范相輔相成的。他曾這樣坦言:“詩人要具備勇于犧牲與奉獻精神,要甘于清貧與寂寞,要富有海闊天高的情懷,崇高而又神圣的心靈,以肩負謳歌時代主旋律為己任,做時代歌者……”我們大可不必用文學評論家的標尺去苛求鄭天送的詩,僅看他心泉里流淌的是“時代歌者”清澈的渴望這一點,就足以有敬重他、關注他、扶持他、鼓勵他的充分理由!
人,應該有一點精神。我認為,這“一點”鄭天送做到了。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