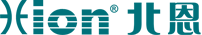|
“小說”,字面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從“小”處“說”起。筆者之所以故意倒置成“說小”說開去,來作為寫這篇序的由頭,是因為我在編輯《余文飛小說選》的過程中,確實鑒賞到青年作家余文飛駕馭小說的“說小”能力以及由此而生發(fā)的“悅讀”魅力。
大凡小說,無論長、中、短、微,都與“說小”密切相關(guān)。所謂“說小”,就是以“說小”而見大,以見微而知著。著眼于“小”,正是對作者駕馭小說能力的具體考核,考核的結(jié)果在于因作者是否擅于“說小”,而對讀者產(chǎn)生“悅讀”魅力的程度。青年作家余文飛的小說,給了我一定程度的“悅讀”魅力。作為既是讀者又是編者進(jìn)而還是作序者的我,不揣淺陋,兼顧這“三者”,對《余文飛小說選》做一番“拼盤式”的縷析歸納和“AB式”的分述鑒賞。
A、“長卷” 、“中調(diào)” 、“短歌” 、 “小令” 這道拼盤式的菜系名曰“小大由之”。
拼盤,屬餐業(yè)用語。是用兩種以上多為冷葷的菜肴擺在同一個菜盤里合成的菜。在此,筆者姑且將《余文飛小說選》類比成文化大餐式的“拼盤”,這個“盤”中“拼”的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微型小說。作者將這套“文化菜肴”,由長到短形象地命名為“中調(diào)”、“短歌”、 “小令”,順著作者的獨具匠心,筆者又以此類推,再加上“長卷”的命名,就使之成為一道“菜系”了,名曰:“小大由之”。顧名思義,作為文化食客的讀者,可根據(jù)各自的喜好選擇“大”“小”了。這對時下文化快餐不同層次、不同口味的需求,無疑起到了供求默契的作用。
“小大由之”順應(yīng)了“忙碌時代”的脈動,要看“小”的,去速讀那些微型小說;要看“大”的,去瀏覽那部長篇小說;要看“不大不小”的,去讀那些中篇和短篇小說是再適合不過了。如此說來,以青年作家余文飛的筆力,巧妙地拉近了讀者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距離,便從理論的層面融進(jìn)實踐的效應(yīng)之中了。說到底,任何作品都不會否認(rèn)它的社會功能,小說也概莫能外。談到細(xì)微之處,不外乎啟迪和消遣功能罷了。綜觀余文飛這些長、中、短、微篇小說,啟迪和消遣功能兼而有之。是“啟迪”了還是“消遣”了?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讀者的理解和認(rèn)知。當(dāng)然,這種理解和認(rèn)知與作品應(yīng)有的“悅讀”魅力是相輔相成的。我有理由相信,余文飛的小說能給了我“悅讀”的魅力,也會理所當(dāng)然地讓更多讀者也能感應(yīng)到這種魅力的。
倘若將這“書”與餐業(yè)的“拼盤”都看作是一種勞動成果的話,二者是多么的相似乃爾!從工序上看,“拼盤”的選料,相當(dāng)于“書”的選材;“拼盤”的制作,相當(dāng)于“書”的寫作;“拼盤”的組合,相當(dāng)于“書”的結(jié)構(gòu);“拼盤”擺上餐桌,相當(dāng)于“書”擺上書架;“拼盤”供人品嘗,相當(dāng)于“書”供人閱讀。“拼盤”到餐桌,要經(jīng)過菜農(nóng)、廚師等多人的協(xié)作,為的是食客的滿意;而“書”到書架,要經(jīng)過作者、編者的多方配合,為的是讀者的青睞。“拼盤”講究的是色香味形,書則講究賞心悅目。這“賞心”就和“啟迪”相扣了,這“悅目”就和“消遣”相連了。 這只是“拼盤”與“書”表層的類比,更深層次的類比,則在于筆者挖掘到這部書具有“拼盤”套“拼盤”的文化效應(yīng)。說到此,就又與筆者“說小”的見地不謀而合地相互牽連了。
這部書 “大拼盤”套了長、中、短、微篇小說的四個 “中拼盤”,而這“中拼盤”又分別套了 “人物、情節(jié)、思想”等若干個“小拼盤”。以上是筆者從“結(jié)果”的角度追溯的展現(xiàn),這“結(jié)果”之源還得從“說小”起始。
B、余文飛擅于在人物塑造上、情節(jié)的架構(gòu)上,思想的深度上,從“小”處著眼,收到了“微而不微”的效果。
其一,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小人物”、惟妙惟肖,富有親和力。
“小”和“大”是相對而言的,“小人物”和“大人物”似乎是一種倫類的劃分,沒有明確界定的分水嶺。這里所說的“小人物”是指生活在社會底層平凡一族,較之那些“大人物”,無論是生活環(huán)境、社會背景還是處世方式,都存有較明顯的差別。
譬如:長篇小說《馬過河》,是以一個現(xiàn)實中存在的某山鄉(xiāng)小村落為原型而進(jìn)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再度創(chuàng)作的。從自然環(huán)境的角度看,這是一處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從社會環(huán)境角度看,這是偏僻貧瘠、交通閉塞、信息不暢、經(jīng)濟(jì)匱乏的小鄉(xiāng)村。作者在這樣的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了不起眼的“小人物”群像。
其實,寫人物,就是寫性格,余文飛深諳此道,他筆下的每個“小人物”都是“這一個”,而不是千人一面。鄢飛龍、曹子蘭、八叔公、英子、凌浪、二丫、麻二、狗蛋、疤頭等,都各有各的脾氣秉性,各自的性格特點。從某個側(cè)面看——或愚鈍、或蒙昧、或魯莽、或狡黠、或粗俗、或齷齪、或狹隘、或嫉妒、或質(zhì)樸、或善良、或義勇、或仗義、或調(diào)皮、或睿智……這多種品性,對每個具體人物而言都各有側(cè)重,抑或兩種或幾種兼而有之集于一身。
這些“小人物”,見不到某類作品塑造的“大人物”讀起來摻假的那種光輝形象,倒顯出食人間煙火的些許平易來。讓我們在平時接觸的人身上,能找到某些似曾相識之處。作者在小處著眼得惟妙惟肖,富有的親和力自然會打動讀者。
其二,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小情節(jié)”栩栩如生,富有感染力。
情節(jié)是小說調(diào)動人物活動的鏈條,“小情節(jié)”是這個鏈條極其細(xì)微的環(huán)節(jié),它類似鏈條的卡簧,具有很關(guān)鍵的精到之處,制約著人物性格的“個性化”。余文飛在“小情節(jié)”的運用上,拿捏得恰到好處。
以《馬過河》為例,整部小說以一串串的“小情節(jié)”描寫了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發(fā)生在小山村馬過河這塊土地上多側(cè)面的生活現(xiàn)狀。以這些“小情節(jié)”,牽扯出鄢飛龍夫妻教書育人的明線,鄢飛龍、曹子蘭、英子淡淡的愛情糾葛的暗線,凌浪、二丫、狗蛋淺淺的情感交織的輔線。這三條線,貫穿作品始終,縱向看去,若干個“小情節(jié)”就像無數(shù)個珠子一樣,穿在這三條線上。
筆者不妨將這些珠子分別命名,它們叫:誤會、猜疑、莽撞、沖動、任性、拘謹(jǐn)、尋根、問底、忍耐、謙讓、曖昧、率真、執(zhí)著、持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珠子本能地發(fā)出了各自應(yīng)有的微光,相互輻射,構(gòu)成了豐富多彩的“小情節(jié)”云集的人文小宇宙。
人物個性是靠情節(jié)表現(xiàn)的,情節(jié)嘛,是情節(jié)套情節(jié)的玩意,那么,從外向內(nèi)看,被套的情節(jié)就是小情節(jié),是大情節(jié)做皮兒,小情節(jié)做餡兒;從內(nèi)向外看,是小情節(jié)生出的大情節(jié),是小情節(jié)做果核,大情節(jié)倒成了小情節(jié)的果肉。皮兒呀,餡兒呀也好,果核呀,果肉呀也罷,都是為了讀者這些食客而營造的。到了這等境地,作者的筆往往不知不覺地被那些“小情節(jié)”鬼使神差,這些“小情節(jié)”一旦萌發(fā),所伸展的枝呀,蔓呀,葉呀就會按照它自身的生長規(guī)律自由成長,這“筆不由己”,是意料之外的收獲。這種意料之外的收獲就這樣降臨在余文飛創(chuàng)作的原野上。
當(dāng)讀者的視野與余文飛創(chuàng)作的原野對接,那《余文飛小說選》的樹上,會有一串串栩栩如生的“小情節(jié)”玲瓏剔透地誘惑著你。摘吧,它不會因為你摘了而化作虛無,而是你摘走一個,它又會冒出一個,繼續(xù)供別人來摘,如此周而復(fù)始,無窮盡也。這就是余文飛筆下“小情節(jié)”的感染力——有點像魔術(shù)啊。
其三、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 “小思想” 有血有肉,富有震撼力。
“小人物”的思想,別于“大人物”的思想,姑且稱之為“小思想”。“小思想”具有草根性,這“小人物”便與“草民”同日而語了。“小人物”的思想帶有一定的赤裸性,可這種“赤裸”并非讓你一眼看透,這不是“含而不露”,而是“露而有含”。“露”的是什么?“含”的是什么?且看余文飛的小說《牛抬頭》——
這篇小說將牛與人的知心知底和盤托出,把斗牛這一血腥的娛樂活動故意渲染得具有一定的世故化,以細(xì)致入微的筆觸鮮活地揭示出斗牛人扭曲的人性,同時也將滿足人獵奇好勝心理的產(chǎn)物——供斗牛人驅(qū)策搏殺的牛的悲慘命運描寫得淋漓盡致。這就與我“露而有含”之言極相吻合:“露”的是,表面的搏殺、血腥和殘忍;“含”的是,牛和斗牛人心理的碰撞與生活歷程的演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生命的探究和思索以及對自然的尊重和順服。更深層次的“含”,則是人類悍然自造出處處可見的“對抗”的劣根和“征服”的貪婪,這給我們帶來的間接啟迪更為發(fā)人深省!從而可以看出,斗牛人這個“小人物”的“小思想”的背后所反映的主題,富有很強的震撼力。這正是我評價余文飛的小說“從‘小’處著眼,收到‘微而不微’的效果”的有力佐證。
小說是借助于人物來反映思想的,“小人物”的“小思想”也同樣如此。余文飛的中短篇小說集《牛抬頭》,收錄了作者發(fā)表在全國各級各類報刊雜志的中篇小說2篇,短篇小說7篇,微型小說28篇,計37篇。可以說這些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書中的每篇小說都是貼近生活的寫作,反映來自這個時代的人性、心理、鄉(xiāng)土等題材,或褒或貶,或抑或揚。作者以“情”的主調(diào),讓每個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情感、思維、遭遇成為埋在文中的一顆顆牽動人心的音符,去感動讀者,使之產(chǎn)生共鳴。
小說《三殺》、《折斷的翅膀》、《秋風(fēng)瑟瑟》、《唐僧師徒經(jīng)商》、《迎檢》等篇什,以關(guān)注社會,關(guān)注民生,直面人生的創(chuàng)作宗旨,把生活中的一些值得深思的現(xiàn)狀或委婉含蓄或直截了當(dāng)?shù)靥宦冻鰜恚瑥亩鴨拘讶藗儗ι睢ι鐣膽n患意識,進(jìn)而引起人們對于社會問題療救的重視。諸如中篇小說《三王》中的棋王、藥王、酒王舍生取義與土匪同歸于盡的壯舉、《網(wǎng)魚》中吉順害死自己的貪婪、《撿來的兒子》中二虎和石花戲劇性辛酸育兒的歷程、《騸匠》中元吉老爹人性的善良、《彎竹箐的吹鼓手》中吹鼓手巧妙的人性拯救,其思想意義的積極向上顯而易見,無不喚起人們從剖析人性的角度,褒善砭惡,激濁揚清。
綜上所述,面對余文飛的小說,愛不釋手,之所以能生發(fā)如此“悅讀”魅力,是因為作者擅于駕馭小說的“說小”能力。這正是——
小說“說小”見功夫,
讀者“悅讀”雅與俗。
君筆根植故鄉(xiāng)土,
并蒂分蘗兩本書。
辛卯年小雪時節(jié) 于北京來風(fēng)軒
(楊楓 作家 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藝術(shù)院院長)
|